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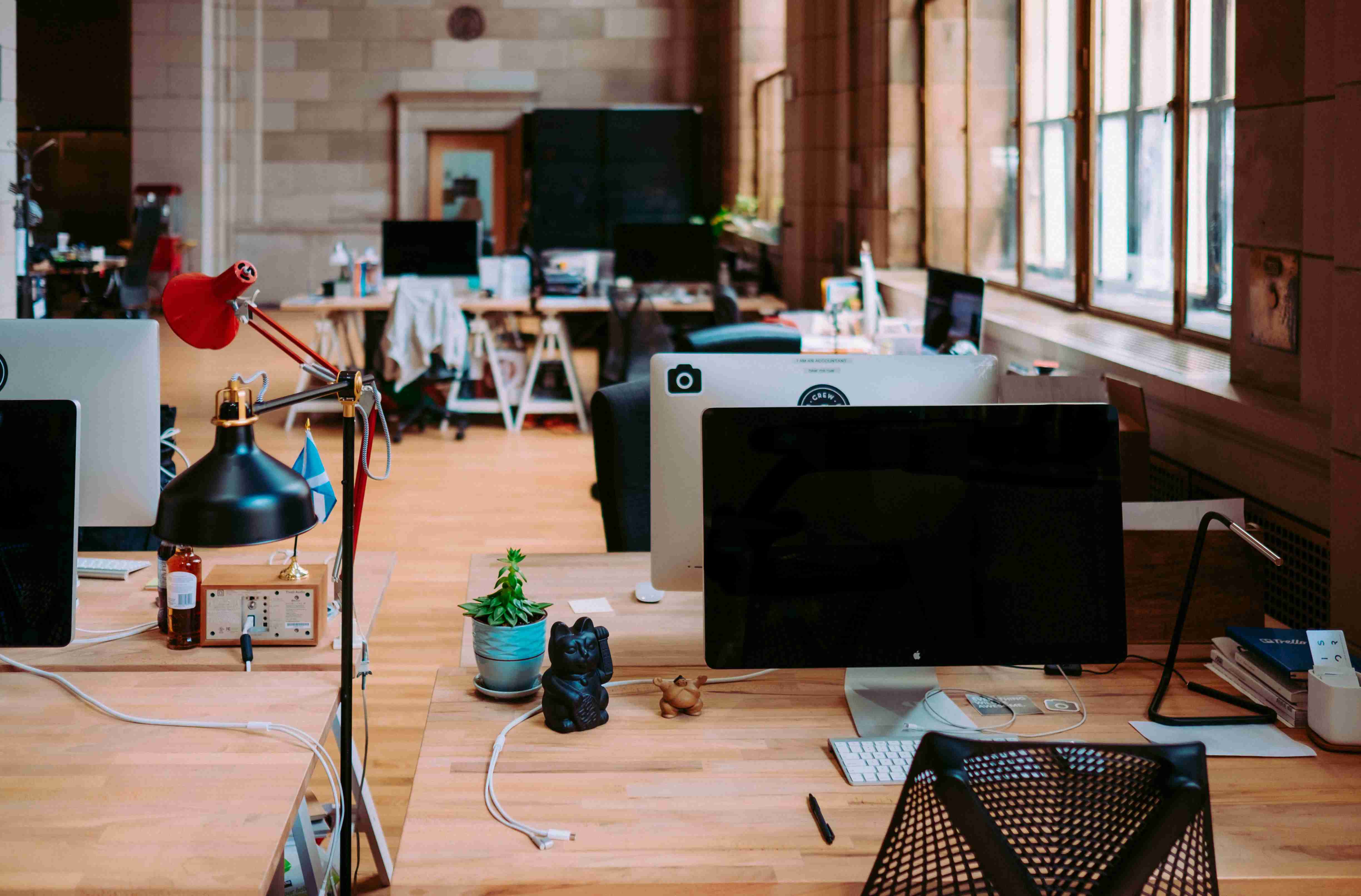
注:本文首发于《法学家》2017年第6期(第158-174页)。
本文共计27,193字,建议阅读时间54分钟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细 目
一、规范意旨与立法争论……1~3
二、概念区隔……4~35
(一)和职务行为……4~17
(二)和表见代表……18~27
(三)和容忍代理(默示代理)……28~35
三、适用范围……36~38
四、构成要件……39~91
(一)客观上具有代理权表象……39~50
(二)代理权外观可归责于本人……51~83
1.可归责性要件之正当化理由……51~68
2.可归责性的内涵……69~79
3.不具可归责性时本人之损害赔偿……80~83
(三)相对人之善意无过失……84~87
(四)因果关系……88~90
(五)时间点……91
五、法律效果……92~103
(一)本人与相对人之关系……92~98
(二)本人与无权代理人之关系……99~102
(三)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之关系……103
六、举证责任……104
一、规范意旨与立法争论
(1)本条系表见代理之规范。在适用上,构成第48条狭义无权代理之例外情形而获优先适用:虽无权代理,不待本人之追认,法律效果仍归属于本人;善意相对人也无撤销之余地。
(2)此条为完全法条,完整展示了表见代理之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除此,《合同法》再无涉及表见代理之条款。所列举之“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三种情形在法律适用上不具区分功能,仅是“无代理权”之现实表达罢了:缺乏代理权在认识上可区分为自始无代理权和代理权嗣后消灭,而所谓的“超越代理权”则可归入二者之一。《合同法》颁行之前,学说中往往将表见代理理解为“授权表示型、权限逾越型和权限延续性”,[1]皆涵盖本人可归责性要素。《合同法》生效后,某些教科书也持如此立场,尤其将“没有代理权”限缩解释为“授权表示型代理权欠缺”。[2]
(3)此条起草中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于“相对人有正当理由相信”之外,附加本人可归责性作为构成要件。[3]这一争论并未因《合同法》的生效而尘埃落定。学说上不乏主张本人可归责性要件者,几有“蔚然成风,其有渐成通说之势”,[4]实务中,明确要求本人可归责性者亦非罕见。[5]《民法总则》(三审稿)第176条将所列举的不具本人可归责性情形排除出表见代理之范畴,此立法模式被最后通过的172条抛弃,采取了和《合同法》第49条并无二致的规范表达[(58)]。
二、概念区隔
(一)和职务行为
(4)法人虽为私法主体之一,然作为抽象存在之组织自然无法亲自行事,必须假手于非仅限于法定代表人之他人——尤其为雇员——在法律行为领域,须借助代理制度完成法律效果之归属,在不法行为领域,假手之人给他人造成损害者,法人依据雇主责任[6]或者执行辅助人制度[7]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我国在上述制度之外,独创职务行为制度。《民法通则》第4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58条被认为构成职务行为之请求权基础。[8]1999年《合同法》生效后,上述条款并未废止,司法实务中仍获大量适用。雇员以法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究竟乃代理行为或者职务行为,和名称称谓问题相比,法律适用上的差异与否和差异所在更值得关注。实务立场可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5)第一,依职务行为,而非表见代理而为判断。既然为雇员,以雇主名义行事,自然归入职务行为,雇主须承担法律效果,无须考虑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即使不构成表见代理也无妨成立职务行为,法院在此仅检查《民法通则》第43条和《民通意见》第58之构成要件,无关第49条之适用。最高院在(2015)民申字第2738号裁定中认为项目经理之行为即使越权,也是职务行为,自然由雇主承担责任,回避了代理权问题。[9]类似地,在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2528号裁定中,法官判定业务经理之行为虽无代理权,不构成代理行为,然而本人仍因职务行为而承担法律效果,并未论证为何非表见代理;进一步,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1848号裁定中,法院明确表示雇员之行为虽不构成表见代理,但属于职务行为,效果直接拘束雇主。[10]
(6)第二,同时依据职务行为和表见代理判断。在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595号、(2015)民申字第418号和(2015)民申字第23号裁定书中,法院认为特定雇员的行为既是表见代理,也是职务行为。
(7)第三,依表见代理制度为断,未涉及职务行为。最高院在(2014)民申字第850号裁定书中着重论证权利外观的可信赖性,认为经理持公司印章具相当代理权表象,构成表见代理,并未阐述是否构成职务行为。相似的,在(2013)民申字第1749号中,信用社负责人在该工作场所和时间内用伪造存单和印章获得存款而为个人所用,最高院认为因第三人非善意无过失,不构成表见代理,未论证职务行为之有无。[11]
(8)第一类裁判立场背后的逻辑是:一定的基础行为隐含着相应的授权,无须考察是否存在额外授权[12];即使并未存在真实授权,既然行为人和本人之间存在相当关系——在此为多为雇佣关系——交易相对人的信赖较之表见代理,更具有合理性,更值得保护。对于后者而言,在具体论证上,法院并不关心是否存在可资信赖的客观表象,也无需判断相对人是否善意无过失,[13]毋宁,法院往往需要费心甄别行事之人是否乃“职务人员”,所行之事是否乃“职务范围”,而“普通雇员”之身份显然不足,须是具有特定权限之特定雇员。
在最高院(2014)民申字第1987号裁定中,法院依据劳动合同、工作会议等,着力检查行为人是否属于工作人员,从而是否属于职务行为,而明确拒绝依照表见代理的要件检验,认为二审法院并未如此作,不构成适用法律错误。在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1236号裁定中,法院认为行为人仅仅是其他部门员工,不是具体负责人,因而不构成职务行为。
(9)然而,事实上,最高院并未始终遵循此裁判逻辑,毋宁,仍存在上述另外两种实务立场。
(10)另外,在“工作人员身份为职务行为之前提”上,最高院在(2015)民申字第1037号裁定中将持委托书之挂靠施工者之行为归入职务行为。
(11)在“特定身份隐含着特定授权”上,最高院在(2014)民申字第536号裁定书中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即使是项目负责人,其行为仍需取得相应授权始构成职务行为。
(12)在“特定身份引发更值得信赖的权利表象上”,法院在“营业厅内的越权行为”一系列案件中,判断标准和立场并不一致:在最高院(2013)民提字第21号判决中,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营业厅内越权签订借款合同构成职务行为,无涉相对人因素;在最高院(2013)民申字第1749号裁定中法院对于类似的案情,则径直依表见代理构成要件为断,着力判断相对人的善意问题。而在“刘雷诉汪维剑、朱开荣、天安保险盐城中心支公司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二审案”(公报案例2012年第3期)中,对于保险公司营销人员的越权行为,法院并未考察职务行为要件,而着重论证代理权外观。
(13)上述裁判思路的重重矛盾从事实层面展现了——无论此区分背后之正当化依据何在——职务行为和表见代理二者的区分难谓成功。
(14)无论冠名为“职务行为”或者“代理行为”,抑或“表见代理”,在法律效果归属上的核心问题皆是权限,在信赖保护上的核心问题皆是权限表象和相对人善意之问题。在此,代理制度(包括表见代理)中的构成要件足以提供清晰的判断标准,实在无须取道在适用中困惑大于贡献之“职务行为”。
(15)在权限问题上,授权行为独立于基础行为,行为人无法从基础行为中获得代理权授予,作为基础行为之一种的雇佣关系也依此逻辑,亦即,一定的职位自身并不能导出相应的权限,职务行为制度在此问题上的预设是错误的。[14]
(16)至于信赖保护,一定的职位在一定情形下确实足以引发代理权表象,这不过是表见代理制度权利表象类型之一罢了[(45)],是否存在权利表象,仍需参度其他因素综合判断,权利表象是否值得保护仍取决于相对人是否善意无过失,亦即,职务并非产生表象,表象并非必然获得保护,职务行为在此问题上的预设也是错误的。
(17)若依职务行为之判断逻辑,代理制度和表见代理制度之构成要件所承载的价值皆落空。由此,《民法通则》第43条和《民通意见》第58条,乃至最高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3条[15]或只能解释为仅具参引意义的不完全规范,而非得独立适用之完全规范:是否得出法人或单位“承担责任”之法律效果,尚需视具体情形结合代理、履行辅助人和执行辅助人等不同的归属规范而定。
(二)和表见代表
(18)《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学说中将其称为表见代表制度。[16]
(19)理论上,我国通说认为,法人代表以法人名义行事时,不具有独立人格,毋宁,其人格被其所代表之法人吸收,此等构造与代理制度迥异,称为代表。[17]依此逻辑,法人代表超越权限行事时自然无法适用第49条之表见代理[18],须创设更加合乎其性质之规范基础,此为第50条之由来。[19]第50条之制度价值在于,“向交易世界宣告,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是法人的行为,并以此最大限度地消除第三人与法人交易的顾虑”。[20]
(20)无论理论前提是否成立,也无论立法者之意图如何,法律之生命皆在适用,与虚妄之理论争辩相比,更值得关注的依旧是第50条和第49条在适用上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差异何在,如此观察第50条独立存在之价值。
(21)从条文表述上看,第50条之“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与第40条之“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在相对人善意之证明上显然不同,在前者,相对人之善意为推定,[21]在后者,相对人须证明自己善意无过失,因此,在交易安全的保护上,前者尤甚。
(22)至于法律效果方面,二者并无差别,皆归属于本人。
(23)如此一来,于实务中,观察对于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以法人名义行事者,法院如何适用法律,或许更有助于我们接近真相。
(24)法院是否仅适用第50条,未适用第49条?在最高院 (2016)民申206号中法定代表人持假印章行事,法院认为法定代表人身份足以使第三人之信赖值得保护,第三人无审查印章真伪之义务,主观上构成善意,适用《民法通则》第43条和《合同法》第50条,判定构成表见代表,未涉及第49条。
与上例不同,在(2013)民申字第1408号中最高院并未适用第50条,而是转向了可称为“表见代表和职务行为之加强版”之《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3条,后者在表述上直接取消了相对人善意之要件。
与上述立场相反,最高院在(2013)民申字第903号裁定中与(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判决(公报案例2009年第11期,“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适用的是第49条,在此最高院认为行为人虽为法定代表人,并持有合同章,但是相对人疏于审查,并非善意,不构成表见代理,法律效果无法归属于法人,并未论证为何不适用第50条。
(25)法院在适用第50条时,是否采与第49条不同之善意推定规则?在(2015)民申字第1043号、(2014)民一终字第270号与(2014)民一终字第109号中,最高院的确如第50条所表述,推定相对人之善意,由本人承担证明相对人非善意(明知越权或者明知内部限制)的举证责任。
然而,在(2012)民提字第156号(公报案例2015年第2期,“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与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振邦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中,最高院则采相反立场,由相对人证明善意无过失。
(26)事实总是能无情地击破我们的大多数想象。由上述例举之裁判立场可知,在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中,法院时而适用第50条,时而抛弃第50条而适用第49条;即使适用第50条,也采用了表见代理制度中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的判断规则,不仅如此,在权利外观的证明上实际上与适用表见代理如出一辙。
(27)由此,表见代理和表见代表之区隔至少在法律适用之具体效用上难谓成功。实际上,第50条解决之核心问题无非是法定代表人之“非越权行为”作为假象应否受到维护,除非立法者秉持“无论是否越权,也无论相对人是否知悉,皆为法人之行为,皆有效”[22]之观念,除非立法者依此抛弃相对人善意要件,实在毫无必要在表见代理之外创设适用范围仅限于法定代表人之表见代表制度以混淆视听,徒增烦恼。[23]
(三)和容忍代理(默示代理)
(28)《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第3句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此条中的“明知而不反对”当解释为默示代理,抑或容忍代理不无疑问。[24]
(29)德国通说认为判例发展出来的容忍代理(Duldungsvollmacht)为与表象代理(Anscheinsvollmacht)并列的表见代理(Rechtsscheinsvollmacht)类型之一,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对于无权代理人的行为而言,前者为本人明知且容忍,从而造成了代理人拥有代理权的假象,而后者为本人不知,不过本人只要尽到注意义务则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25]
(30)少数学者认为,既然司法实践中一直承认意思表示的内容当从交易相对人的角度予以解释,那么,针对代理权是否授予及其具体范围,在内部授予上,则依代理人角度为断;在外部授予上,自然须依交易相对人之合理理解为准,依此逻辑,在代理权授予不需要特别形式之场合,“明知而不反对”显然属于可从交易相对人角度理解之“默示代理”。[26]
(31)如此一来,“明知而不反对”的性质之争当表述为,有权代理之默示代理抑或(广义)无权代理或表见代理之容忍代理或更妥当。
(32)上述争议,并非仅具学术讨论中概念辨析之价值,毋宁,对法律规则之适用之影响具相当影响,其中最为重要者当属是否可撤回[27]:如解释为默示代理,自然可如明示代理权授权一般,准本人撤回授权;[28]如解释为表见代理之容忍代理,自无此规则适用之空间,因为,可归责性权利表象的发生既非基于法律行为也非基于准法律行为[29]。
(33)余以为,“明知而不反对”至少并非纯正之默示代理,这一事实当作如何解释,恐需借助类推,至于当类推至何种既有规则,自然须考虑法律效果之可接受与否以及推理之便捷与否此两种因素,亦即,目光须在结果与开端之间“流转往返”。
(34)如将其类推适用默示代理制度,允许本人撤回所谓的授权,不可回避的问题则是,如果本人之撤回不足以消除相对人对于代理权存续或者代理权范围的疑虑,亦即,如果撤回本身再次引发代理权表象,又当依何种规则为断,此时是否仍须借助表见代理。由此,莫不如从发生“明知而不反对”之时,则引入表见代理规则更为便宜,从而代理权的撤回转换为摧毁代理权表象问题。
(35)如此看来,“明知而不反对”无论是否冠于容忍代理之称谓,均当解释为广义表见代理之一种,和“稍加注意即当知晓”皆属于《合同法》第49条之表见代理,二者在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上并无差别,[30]二者之区分仅具清晰认识之功能罢了。
三、适用范围
(36)第49条虽未明示适用范围仅限于意定代理,在解释上亦当作此理解。
(37)法定代理制度目的在于补足与扩充不完全行为能力者参与交易之机会,自然不得令受保护者承受违背其意愿并且多半损及其利益之法律后果。[31]
(38)另外,作为表见代理构成要件之一的与真实情形不符之代理权外观,在法定代理之处并不存在:法定代理权之有无与范围皆由法定,如何产生假象?实务中鲜见就法定代理人之行为主张表见代理者。在云南高院(2016)云民申928号裁定中,相对人主张法定代理人之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法院未直接回应,而是适用《民法通则》第18条之“不得损害被监护人利益”结合《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认为“本案《抵押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的规定,损害未成年人吕某的利益,为无效合同。”
四、构成要件
(一)客观上具有代理权表象
(39)本人之所以在无代理权的情形下仍需为他人行为负责,原因在于相对人对于代理权的存在具有一种合理的信赖。这一信赖自然需要事实上的依据,相对人毫无根据的错误想象并不受到保护。亦即,无权代理人如同代理人一样行事。
(40)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何种情形构成了足以引发合理信赖的代理权表象。
(41)如有权代理一般,通常情形下行为人须以本人名义行事,这是代理行为显名主义(Offenkundigkeitsprinzip)之要求,本条“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则为此意。最高院在(2016)民申2628号裁定、(2016)民申2278号裁定、(2015)民二终字第64号判决、(2014)民四终字第51号判决以及(2012)民申字第93号裁定中强调“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之一是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于仅具行为人名义的情形拒绝承认表见代理。在最高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层级上,未见“虽无本人名义,也构成表见代理”者。
(42)然而,既然在有权代理,一定情形下亦无须显名——在某种交易中,相对人从周遭情境可推断出行为人乃为他人行事之代理人,且本人之身份并不重要或者可推知本人之身份,自然无须苛以“本人名义”要件——表见代理自然依此逻辑。《民法总则》第172条对名义问题并未作要求,仅规定“实施代理行为”。
(43)无权代理人将法律效果归属于本人之主观意愿并非必须。[32]实务中,无权代理人行无权代理之事的目的往往恰是“利益归于自己”,未见法院以此为由拒绝承认构成表见代理,毋宁,仅需从客观上看,具有效果归属于本人的代理结构即可。
(44)在怎样的情形足以构成代理权表象这一问题上,抽象的说词对于法律适用之作用或许远不如案件类型总结。案件主要类型包括:
(45)第一,无权代理人具特定身份型。持合同章之法定代表人[33]、曾经的股东监事持本人之印章[34]、之前为代理人的股东[35]、项目经理[36]、挂靠人持虚假授权书[37]、借用建筑资质的实际施工人[38]、董事长之妻舅持公司印章[39]构成代理权表象;父子关系[40]、虽为监事和大股东但无其他授权之表象[41]、无权代理人与本人并无特别关系且无其他授权表象[42]、银行工作人员在工作场合使用假存单[43]、未曾长期为代理人之职工[44]不构成代理权外观。
(46)第二,外部授权或外部告知而内部撤回或限缩型。内部撤回对项目经理的授权而未外部告知[45]、外部授予房屋销售权而仅内部限缩[46]、法定代表人被撤职并未变更工商登记[47]等情形,构成代理权外观。
(47)第三,持代理权凭证型。中国背景下,授权书和印章在交易中对于身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示作用。实务上,持本人之印章或授权书而为无权代理者,极为常见。而虽已内部撤回代理权但无权代理人仍持授权书[48]、虽不具特殊身份但持有本人之印章[49]构成代理权外观。
(48)第四,本人事后履行型。原理上,权利表象须在行为实施的时候存在,本人此后的行为仅能理解为对之前所实施的无权代理的追认,不能作为判断表见代理的基础。[50]然司法实务中不乏将本人事后的履行视为代理权表象者。[51]
(49)第五,长期无权代理而本人并未反对型。最高院在许多判决与裁定中并未如德国判例般区分容忍代理和表象代理,行为人长期行无权代理之事,而本人明知而未反对,皆构成第49条之表见代理,[52]仅在(2016)民再76号判决中明确表示本人之明知构成了默示,当属于有权代理,非以无权代理为前提之表见代理,至于这一判断是否仅为无关法律推理之称谓选择问题,此简短的判决书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
(50)必须强调的是,上述仅是既有裁判规则的描述罢了,并非裁判思路的综合总结,更不具相当的裁判指引功能,毋宁,在代理权外观上,看似大致相同的案情,法院的判断也不尽相同,几乎任何一种类型都存在相反的判决结果,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复杂程度。
(二)代理权外观可归责于本人
1.可归责性要件之正当化理由
(51)代理权外观之形成须可归责于本人(Zurechenbarkeit des Rechtsscheintatbestands)。在表见代理中,本人承受了与自己意愿相悖的负担——如同有权代理——在此等与被奉为私法之圭臬之意思自治原则显然不符的法律安排中,本人之利益被牺牲,交易相对人获优待,此种利益之倾斜自然需要辅以除了代理权外观要件之外的与本人相关的因素始获得更大程度的正当性,[53]亦即本人须以可资谴责的方式诱发了权利外观,本人只要尽到注意义务就能够知道他人无权代理,而且本来可以阻止。[54]
(52)规范层面上,《合同法》第49条是否包含可归责性要件,学说上和司法实务中素有争议。
通说认为,第49条中立法者并未明确承认本人可归责性要件,[55]其中有观点主张,既然第49条文义未包含可归责性要件,实不宜贸然抛弃立法立场,莫不如借鉴法国法,将本人与外观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内置于相对人“合理信赖”因素。[56]另有观点认为,当限缩解释第49条,将非归因于被代理人之法律外观排除出“有理由相信”之外;[57]有作品独辟蹊径,从《合同法》第48条中善意相对人拥有撤销权的立法立场出发,推论相对人善意与否并非狭义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之区别,因此第49条中当隐含本人归责性要件。[58]
(53)实务裁判中明确指出本人之可归责性乃表见代理构成要件之一的可谓凤毛麟角,偶见者大多集中在南京中院和江苏高院所做之判决或裁定。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长汽开民初字第974号中,法院直言由于授权书系伪造,“享有代理权外观的形成不可归因于李金凤,亦不构成表见代理”。江苏高院(2015)苏商终字第00275号中,初审法院则进一步将“行为人实施了无代理权的行为、且所存在的代理权表象与被代理人行为直接相关并在被代理人风险控制能力范围内”与以本人名义实施代理行为、第三人善意无过失一并解读为《合同法》第49条的构成要件,并据此判定本案中本人虽未授予代理权,但是在多个场合允许无权代理人以其代理人身份行事,因而代理权之表象和本人直接相关,且完全属于本人可控制范围,从而充分可归责要件,[59]二审法院(江苏高院)虽以不具权利外观为由否定表见代理,未见对初审法院所持可归责要件主张之回应。
类似立场的有,广东高院(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2724号之“无权代理人伪造印章不具有本人可归责性”、宜兴中院(2014)宜民初字第2423号之“印章管理不严构成本人之可归责性”、南京中院(2016)苏01民终5937号之“未对外披露挂靠关系且允许刻制印章构成本人之可归责性”、南京中院 (2016)苏01民终2366号之“未参与权利表象之形成因而本人不具可归责性”、南京中院 (2016)苏01民终2425号之“本人交付印章构成可归责性”、佛山中院(2013)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005号之“无权代理人伪造印章不具有本人可归责性”。
(54)最高院公报刊载的涉及表见代理的5个案件[60]以及最高院作出的和表见代理或者职务行为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244项判决与裁定中[61],均无明示本人可归责要件者。
(55)不过若以此为断,认为我国司法实务在判定表见代理时从不考虑本人可归责因素则或许过于武断:在某些被判定构成表见代理的案件中,本人往往也具有可归责之处,而在某些被判定不构成表见代理或者职务行为的案件中,则明显缺乏本人可归责性,法院在此或许不过以“是否具有代理权表象”[62]或者“相对人是否非善意无过失”[63]为名隐晦[64]地考虑了本人因素罢了。
(56)当然,与上述考虑本人因素立场相反,在某些案件中,即使具可归责情形,法院仍拒绝承认构成表见代理;[65]在不具本人可归责性案件中,法院也可能承认构成表见代理[66]。
(57)在可归责问题上,中国法院的态度模糊、摇摆、矛盾、混乱,几乎不存在一贯的立场。
(58)《民法总则》三审稿(2016年12月27日提交审议)第176条虽沿袭第49条立场,未在“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之外一般性地增加额外构成要件,但明确排除了一系列显然不具本人可归责性的情形。这一排除条款被最终通过的《民法总则》第172条全部删除,其在文字表述上和第49条几无二致。此番删除原因何在,能否解读为立法者明确拒绝了本人可归责要件未可知。
(59)比事实描述更重要的是正当性问题。法律非经解释不得适用,被称之为规范解释的每一次法律推理中皆包含了解释者的价值判断,此间,规范之当为与规范之实为委实无法切割,倘若目前甚为流行之法解释学,其内涵乃“严格遵照文义”或者一定程度上“探究立法者真意以诠释文义”,那么作为科学之法学的存在价值颇值得怀疑,缺乏反思和质疑的法学研究恐将沦为“政治的婢女”。[67]因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毋宁是,应否在法价值的应然层面上引入本人可归责性要件。
(60)赞成者多沿袭德国法上的表见代理制度之路径,认为不应拘泥于第49条的文义,当以一定价值取向为基础将本人可归责性作为构成要件之一,以为法律漏洞之填补[68]。此等价值取向之问题,自然无谓真假,构成论证之基础的不外乎哪个选择更加合乎体系,哪个选择更有助于规范目的之实现。
(61)表见代理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同为权利外观责任,二者在构造上颇为类似。
(62)德国通说认为,脱手物不适用于善意取得,在这里本人并没有引发权利表象,相对人的保护由此退居其次。[69]同一逻辑下,德国民法典第170条以下诸条款以及判例所发展出来的容忍代理和表象代理制度中,皆有本人可归责性要件。[70]
(63)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并未采上述立场,并未将非脱手物设为构成要件之一,[71]毋宁,遗失物[72]和盗赃物[73]皆有适用善意取得之余地,端看相对人是否构成善意无过失。由此立场出发,表见代理制度中不必考虑本人因素似更具“体系一致”。[74]
(64)然余以为,我国将脱手物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之立法抉择颇值得商榷,如若仅为了保持“评价一致”而令表见代理制度仿造之,无异于重复错误。在此背景下,在表见代理中承认本人可归责性,虽与既有善意取得规则判断龃龉,亦无妨。
(65)和善意取得制度相似,表见代理之规范意旨显然在于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自本人角度而言,则是课以严厉之法律效果,以敦促其控制风险,倘无论其能否有机会或者有能力控制风险皆须承担如同有权代理之法律效果,无异于无咎者也受惩罚,规范之指引和风险分配功能将大打折扣。
(66)何况,第49条虽列举了“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三种可能发生表见代理之情形,但是此种区分恐怕仅具无涉法律决策的事实描述功能,难谓有法适用上实质效用[(2)]:无论何种情形,均适用“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这唯一要件。这和德国民法将表见代理制度视为须具备相当正当理由的法秩序之例外规则、不同情形构成要件不同之立法例,旨趣大异。
(67)划分越细,则规范适用之恰当性更为可靠,法律判断也更合乎事物之性质。第49条在构成要件上如此大而化之的规范模式或赋予法官无穷的裁量空间,使本来饱受“他治”之诟病的表见代理制度,在我国恐沦为更加危险的制度。在此背景下,担负限制法官恣意和对案件事实提供更为清晰的观察视角之现实功能的本人可归责性要件难谓无用。
(68)实际上,从第49条“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之文义亦可导出本人可归责性要件,[75]此处之“有理由”并非事实层面之描述,乃蕴含法价值判断之规范要求:相对人之信赖自然须在通常情形下合理而非疏忽轻率,此外,倘若该权利外观并非可归责于本人,则相对人之任何“信赖”皆可排除出“合理”之范围,从而不构成“有理由相信”。[76]
2.可归责性的内涵
(69)所谓本人之可归责性,系指本人以一种可归责的方式引发了代理权表象,本可以阻止却不阻止,本来可以摧毁权利表象却不作为。[77]
(70)如代理权消灭或限缩后未能及时收回代理权凭证[78]与未能及时消除代理权表象[79],则为本人对于代理权表象之形成具可归责性。印章[80]或授权书[81]被盗或被伪造、仅仅“内部管理混乱,用人失察”[82]则不足以成立本人可归责性。[83]
(71)在此,仅仅在客观上诱发权利表象是不够的,本人必须具有过错。[84]权利表象仅有在如下情形下才可归责于本人:本人知道或者只要尽到注意义务就能够知道,而且本来可以阻止。[85]
(72)这里的过错,当然并非违反了法定义务(eine verschuldete Rechtspflichtswidrigkeit),而是一种对自己事务的漠不关心:本人违反了不真正义务(Obliegenheitverletzung)[86],轻过失已足[87]。
(73)另外一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涉及足以将表见代理制度釜底抽薪的质疑:既然本人仅仅是过错地违反了不真正义务,为何承担的不是损害赔偿,而是由其径直在法律行为领域承受法律效果,这种法律安排显然缺乏法律行为领域的意思自治要素。[88]既然第49条已明确承认表见代理制度,这一立场也被《民法总则》第172条全盘继受,那么此诘问在中国法上的现实意义则转化为法院当谨慎判定表见代理。
(74)倘若乃第三人而非本人以可归责的方式引发了代理权表象,那么是否以及根据何种法律制度将第三人的行为归于本人,虽迄今未见相关裁判,在逻辑上,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75)在请求权基础上至少履行辅助人制度可资适用[89],我国并无债法总则,也未一般性地规定履行辅助人制度,将第三人行为归于本人的制度由《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监护人责任[90]、第34、35条的雇主责任、《合同法》第121条的因第三人原因违约等,上述规范的法律效果均是损害赔偿,不涉及法律行为领域的效果归属问题,因此,此问题的解决目前仍须仰赖法官创造性地引入履行辅助人[91]或者突破性解释代理制度:至少本人应当对其可控制范围内的第三人的行为负责。
(76)一般说来,可归责性在任何情形下都以自愿行为和行为能力[92]为前提,无法通过法律行为负担义务的人,自然也就无法制造具有可归责性的权利表象。[93]
(77)至于本人是否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应当知道”(Kennenmüssen)权利表象之存在才具可归责性,则须区分不同情形。
(78)如果本人通过某种积极行为创造了代理权表象,尤其是赋予某人某种职位,且通常情形下,该职位往往意味着获得代理权或者一定范围内的代理权限,那么,则无需额外检查本人是否“应当知道”代理人之行为。[94]例如,项目经理、[95]挂靠人[96]、公司经理[97]和项目部工作人员[98][(8)]。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积极行为”都足以构成权利表象,而是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可作此理解。
(79)为了排除可归责性,本人必须摧毁已经形成的假象,仅内部阻止无权代理人行为是不够的。[99]
3.不具可归责性时本人之损害赔偿
(80)代理权表象不可归责于本人时,自无法构成表见代理,法律效果无法归属于本人。然本人未能妥善保管代理权凭证或者用人失察的,是否对相对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呢?
(81)可能的请求权基础之一是《合同法》第42条第三项“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之缔约过失责任,亦即,本人和相对人之间曾经存在以缔约为目的的特别接触,而本人对于而无权代理人的行为具有本条意义上的过失[100],本人则须负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101]单纯的管理不当,并不会构成缔约过失。[102]
(82)中国法背景下,可能的请求权基础之二是《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中“财产权益”结合第6条第1款之侵权损害赔偿,乃所谓的纯粹经济利益损失保护问题,[103]此请求权基础亟待案件类型总结以明确其构成要件。
(83)实务中,鲜见本人不具可归责性时对相对人负损害赔偿之案例,更未见以上述请求权基础判令本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者,仅在(2013)民申字第1749号中,最高院认为虽不构成表见代理,但本人“存在过错”,应对相对人承担“补充责任”,然并未明示法律依据。
(三)相对人之善意无过失
(84)假象虽假亦为真之基础在于存在值得保护的信赖(ein schutzwürdiges Vertrauen),在此相对人之善意为不可或缺之因素,亦即,相对人不知亦非应知代理权瑕疵,此乃第49条之“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之应有之义。虽条文并未明示此处之善意是否意为善意无过失,但“善意无过失”之构成要件经由最高院在多个场合的强调,几已获实务之一致肯认。[104]
(85)司法实务中,法院往往并未明确区分代理权外观和相对人善意无过失要件,通常以相对人是否足够谨慎,是否已尽审查义务为依据判断是否存在足以引发合理信赖的权利外观,鲜见严格区分者。[105]至于,是否进一步要求“善意且无轻过失”[106]则未见相关裁判。
(86)实际上,在权利外观信赖保护制度上,什么时候第三人的不知悉是可谴责的,法律的回答是不同的。[107]在善意取得上,《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15条要求受让人不知道处分权瑕疵且无重大过失,对于表见代理自然不必要求与其保持一致,核心问题是第三人何种程度的审查义务是可期待的,在此,并不存在统一的审查义务(不真正义务),毋宁,应根据不同情形分别判断,由此,具有决定的意义是个案,当然,第三人善意与否乃秘而不宣之主观状态,需结合客观情势而为判断[108]。
(87)一般而言,未要求行为人出示授权书构成非善意,[109]即使行为人具相当身份,授权书之要求也非多余,[110]至于授权书上的印章之真伪通常不属于相对人审查义务范围[111];行为人具有指向代理权外观的一定身份,但是明显超越权限,相对人也难谓善意;[112]对于特殊的不寻常的交易——特别是金融领域或者金额巨大的交易——相对人须更为谨慎,轻率、仓促以及有疑问时未能询问本人或者要求行为提供更多的彰显代理权的证据,均构成非善意。[113]
(四)因果关系
(88)相对人信赖代理权假象为真而实施法律行为,而且倘若不获信赖保护制度之保护则必然遭受不利益,唯有如此相对人才有受到保护之必要。[114]第49条虽未明确规定因果关系要件,亦不妨其作为信赖保护之当然前提。
(89)理论上,因果关系可分为如下两种:代理权表象和信赖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信赖和法律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115]对于前者如果相对人根本不知道权利表象,也并非基于信赖权利表象而行事,则不存在值得保护的信赖。亦即,相对人须确实知晓代理权表象,此乃和不动产善意取得中对登记之抽象信赖不同的具体信赖。[116]在后者,倘若相对人知晓代理权瑕疵也会实施法律行为,则缺乏此因果关系;这一要件仅在极少数的情形下有意义,因为大多数情形下,信赖和法律行为之间缺乏因果关系之案件中相对人并非善意无过失[117]。
(90)实务中,未见区隔于上述三个要件,单独讨论因果关系之裁判。
(五)时间点
(91)代理权表象、本人之知悉或者应当知悉与相对人之善意无过失之状态须在无权代理人行为实施时存在,本人事后之知悉[118]与履行[119]只能解释为对于无权代理的追认,并非成立表见代理;相对人在缔约之后始察觉代理权瑕疵亦无妨构成善意[120]。
五、法律效果
(一)本人与相对人之关系
(92)对于相对人而言,表见代理补足了代理权之瑕疵,在法律效果上如同有效之意定代理,无权代理人之行为效果归属于本人,在合同,本人和相对人成为合同之当事人[121],第49条中“该代理行为有效”应作此理解。
(93)表见代理抑或代理制度皆乃归属规范,回答的问题仅是谁承担法律效果,并非法律行为效力判断规则,自然无法保证相对人和无权代理人缔结之合同必然有效,毋宁,在效果归属判定完毕之后,当引入无效、可撤销以及效力待定等法律行为效力规则予以衡量,亦即,受表见代理制度保护的法律行为也可能存在其他效力瑕疵。[122]
(94)最高院在(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判决[123]中则独辟蹊径,将合同有效作为表见代理之构成要件之一:“因本案基本授信合同及相关贷款合同,均为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且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在本案所涉贷款过程中具有过错,故本案不适用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且不论所适用之“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型无效事由存在之价值及其对私法自治之不当干涉,如此叠屋架床的推理模式恐怕仅是为了除去“表见代理中法律行为必然有效”之法律后果的“事先防御”,然此举曲解了表见代理仅作为效果归属规范之制度价值,令其不堪重负。
(95)所幸上述立场并未被最高院完全遵守,在(2016)民再386号[124](2015)民申字第1152号[125]和(2015)民申字第426号[126]强调代理人的行为纵使构成犯罪,亦不影响法律效果归属于本人。
(96)关于相对人能否放弃表见代理之保护,转而选择狭义无权代理,在本人追认之前依据第48条第2款第3句撤回自己之意思表示,从而从合同束缚中获得解脱或者依据第48条第1款选择无权代理人承担责任这一问题,司法实务中尚未见相关裁判。
(97)我国学说多持肯定立场。[127]德国学界颇有争议,通说认为相对人并无选择权。[128]有观点认为,对于相对人而言,表见代理乃为其利益而存在之保护机制,自然可以放弃;无论通说如何反对这一选择权,相对人皆可通过在诉讼中通过放弃表见代理之诉讼请求而达成,这一安排可使预计到表见代理之较重的举证负担几无法达成的相对人转向无权代理制度之保护。[129]
(98)自理论上而言,既然相对人信赖代理权表象,以本人为交易对象而为交易,那么维护假象,使法律效果如同有权代理般归属于本人自然是尊重其意思自治之当然之意,若允许相对人此时另行选择无权代理,岂非事后反悔?有权代理之时,尚不允许相对人如此选择,表见代理之下相对人为何获此优待?
至于诉讼中的诉讼策略则不可解释为事实上存在上述选择权,此时表见代理尚未经证明,如何构成法律上的事实,相对人如何在不存在之表见代理和无权代理之间作出选择?[130]
(二)本人与无权代理人之关系
(99)本人因表见代理而承受了违背其意愿之法律效果,此损害乃无权代理人之行为引起,自当由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3条规定:“被代理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承担有效代理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后,可以向无权代理人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即为此意。
(100)损害赔偿之请求权基础视本人和无权代理人之间是否存在内部关系以及存在何种内部关系而定,[131]如果无权代理人和本人之间存在契约——通常是委托合同和雇佣合同——请求权基础可能是违反契约,如果二者之间并无法律关系,请求权基础可能是无因管理和侵权。
(101)实务中,鲜见明示请求权基础者。[132]
(102)理论上,无论何种请求权基础,倘若本人对于代理权外观之发生存在亦有过失,则无权代理人之损害赔偿范围可依据与有过失制度获减轻。[133]因立法中并无债法总则之缘故,我国实证法上并无统一适用于损害赔偿领域的与有过失制度,这一制度被分别规定于《合同法》第119条第1款与《侵权责任法》第26条。但立法之缺漏并不妨碍法院类推适用既有规则,在本人对无权代理人主张损害赔偿时寻求与其他损害赔偿领域评价一致之解决方案。
(三)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之关系
(103)表见代理补足代理权瑕疵,法律效果如同有权代理,无权代理人和相对人之间并无任何法律关系。
六、举证责任
(104)相对人就代理权表象、本人可归责性以及相对人善意无过失要件承担举证责任。[134]最高院审理的案件中,虽有极少数采相反立场,[135]基本遵循此举证规则。[136]
注释:
[1]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89-292页。类似观点有,佟柔之“对第三人表示已将代理权授予他人,交付证明文件与他人,代理权授权不明、代理关系中之后并未采取必要措施,佟柔,《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第212页;马俊驹之“由代理权限制所生的表见代理,由授权表示所生的表见代理以及由代理权的撤销和消灭所生的表见代理”,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06-307页。奚晓明针对“没有代理权的表见代理”所列举之“未授权的外部告知、交付证明文件、允许他人挂靠或者作为自己的分支机构行事、允许承包人以自己的名义行事以及明知无权代理而不反对”,奚晓明,《论表见代理》,《中外法学》1996年第4期,第32-33页。
[2]孔祥俊,《合同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5-186页;
[3]参见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立法资料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页。赞成者,尹田,《论“表见代理”》,《政治与法律》,1988年第6期;反对者,佟柔,《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章戈,《表见代理及其适用》,《法学研究》1987年第6期。
[4]冉克平,《表见代理本人归责性要件的反思与重构》,《法律科学》2016年第1期,第73页。
[5]最高院 (2013)民提字第95号(公报案例2015年第7期,“李德勇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云阳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6]《侵权责任法》第34条虽在用语上特立独行,摒弃雇主责任和执行辅助人之内涵更为确定之表达,采用“用人单位、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的责任”之新鲜语词,然其所规范者和上述制度并无二致,不妨删繁就简,称之为雇主责任更为便宜。英美法中雇主责任为替代责任,亦即,雇主代人(雇员)受过,并不能以自己在选任和监督上并无过错而免责。Paula Giliker, Vicarious Liability in Tort 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7]德国民法典第831条及以下条款所采立场是:执行辅助人实施不法行为时,雇主为自己在选任、监督和配备工具方面的过错(被推定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8]最高院在适用此两条的56个案件中,皆将其称为“职务行为”。依以上述两条的适用为检索对象在威科先行数据库检索之结果为断(截止至2017年5月17日)。
[9]相似立场:最高院(2014)民申字第1653号。
[10]相似立场: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3298号、(2014)民申字第1987号(若无特别说明,同一句子中的裁判,其审理法院同为首案号所示之法院)。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2158号:未对再审被申请人关于“无代理权表象,未构成表见代理”之的回应,径直根据职务行为判定本人承担法律效果。
[11]相似立场:最高院(2013)民申字第312号:虽为负责人,但是明显超越权限,第三人难谓善意,不构成表见代理,没有论证为何不是职务行为。
[12]最高院(2014)民申字第525号:仅有“项目部副经理”之特定职务,无特定授权,也认定为职务行为。
[13]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1111号和(2014)民申字第213号。
[14]最高院(2014)民抗字第31号中明确表示,一定职务隐含一定授权。
[15]适用此条,将他人行为几乎无条件地归属于本人时,法院须甄别“一般工作人员”和“负责人”(最高院(2013)民申字第2016号),须甄别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最高院(2016)民终801号),前一要件尚可解释为权利表象之可信赖程度,后一要件实在匪夷所思:行为人之行为受到外部秩序消极评价愈甚,法律效果愈易于归属于本人?依法理,此条欲解决之问题和表见代理并无二致,皆乃假象是否为真,法律行为效果是否归属于本人。在构成要件上,第3条较之表见代理,显然更为简化,表象之可信赖性和相对人之善意皆不在其列。自1998年4月该条生效以来,最高院适用其之裁判共27则(截止2017年5月4日,威科先行数据库检索结果),在这些裁判中,法官皆严格遵循其文意,并未额外要求任何要件,更无《合同法》第49条适用之空间。例见,(2016)最高法民申1017号、(2016)最高法民申2143号和(2015)民申字第3566号。若此条被视为排斥《合同法》第49条之完全法条,则表见代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实无适用之空间了。
[16]李建华,许中缘,《表见代表及其适用——兼评<合同法>第50条》,《法律科学》2000年第6期,第7-8页。
[17]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4版,第131-132页。
[18]朱广新认为,第50条之理论基础并非表见代理之权利外观理论,而是法人内部和外观关系之区分理论。朱广新,《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中外法学》2012年第3期,第502页。有观点进一步认为,应抛弃所谓的表见代表制度,采用更符合法人本质的越权规则:无论相对人是否知悉,法定代表人之行为皆属于法人之行为。耿林、崔建远,《民法总则应当如何设计代理制度》,《法律适用》2016年第5期,第60-61页。
[19]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422页。
[20]注18,朱广新文,第502页。
[21]沈德咏、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第102-103页。
[22]参见注18,耿林、崔建远文,第60页。
[23]《合同法(试拟稿)》(第三稿)(1996年6月7日)曾在第43条对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和表见代理作统一规定,“考虑到民法代表制度与代理制度的类似性,及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与表见代理的类似性,将其合并规定在第三稿第三章关于代理问题的第43条,安排在表见代理的规定(第2款)之后,作为第43条的第3款:“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法律、章程规定的权限订立的合同,准用前款规定”。”梁慧星,《关于中国统一合同法草案第三稿》,《法学》1997年第2期,第47页。《民法总则》第61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此条与《合同法》第49条以及《民法总则》第172条在适用上之关系,尚待充足的实务案例以揭示。
[24]关于此条之立法背景考察、学说争议梳理和理论解释方向,最具参考价值的是,杨代雄,《容忍代理抑或默示授权——<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第3句解析》,《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4期。有观点认为,本规范不宜解释为对无权代理的拟制追认,参见张家勇,《两种类型,一种构造?——<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第3句的解释》,《中外法学》2012年第3期。
[25] Heinrich Palm, Kommentar zum § 167, in: Erman Kommentar zum BGB, 12.Aufl., Otto Schmidt, 2008, Rz.7.
[26] Eberhard Schilken, Kommentar zum § 167, in: Staudinger Kommentar zum BGB,Berlin: Sellier-de Gruyter, 2009, Rz.29.
[27]最高院(2016)民再76号中,最高院认为依《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第3句,行为人之行为因本人“明知而不反对”构成了有权代理,二审法院表见代理之认定属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判决全文未回应本人(再审申请人)关于相对人非善意的意见,背后逻辑似乎是,如果“明知而不反对”视为有权代理,自然无须讨论表见代理制度才有的相对人善意与否问题。此逻辑显然有误,即使视为有权代理之默示代理,也是从相对人角度解释之结果,相对人的善意与否显然至关重要,在这方面,默示代理或者表见代理的解释路径并无差异。
[28] Jürgen Ellenberger, Kommentar zum § 172, in: Palandt Kommentar zum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70. Aufl., München: C. H. Beck, 2011, Rz.9. 德国通说和联邦最高法院均反对撤回,Schilken认为,既然(狭义的)容忍代理实际上就是默示的代理权授予,自然可以撤回。参见注26, Rz.29.
[29] Karl-Heinz Schramm,Kommentar zum § 167, in: Münchener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5. Aufl., München: C. H. Beck, 2006,Rz.53.
[30]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1413号:本人的默认引发了代理权外观,构成表见代理。相似立场:(2015)民二终字第335号、(2012)民一终字第65号。
[31]类似观点参见,汪渊智,《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解释论》,《政法论丛》2012年第5期,第98页。反对观点参见,董瑜芳,《表见代理的表现及其归责原则》,《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32]德国通说也作如此见解。参见注26,Rz.39.
[33]最高院(2013)民申字第903号。
[34]最高院(2016)民申2553号。
[35]最高院(2013)民提字第140号。
[36]在项目经理持假章借款案((2015)民申字第3065号)中,法院认为是否假章并非第三人的审查义务此乃本人内部管理不严导致,项目经理这一身份足以构成权利表象。同此判决立场的有: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3341号、(2015)民申字第1620号、(2013)民申字第1568号。
[37]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3402号、(2013)民申字第600号。
[38]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1217号。在类似案件最高院(2013)民申字第1114号中,法院判定出借人和借用人承担连带责任,并未论证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39]最高院(2014)民申字第1847号。
[40]最高院(2014)民申字第657号。
[41]最高院(2014)民提字第175号。
[42]最高院(2014)民申字第1629号
[43]最高院(2013)民申字第1749号。相反观点见“刘雷诉汪维剑、朱开荣、天安保险盐城中心支公司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二审案”(公报案例2012年第3期):保险公司营销人员在保险公司设立的营销部使用加盖伪造保险公司业务专用章假保单,构成代理权外观。
[44]最高院(2014)民申字第536号。
[45]最高院(2014)民申字第1242号。
[46]最高院(2012)民抗字第24号(公报案例2014年第1期,“湖北金华实业有限公司与苏金水、武汉皓羽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案”)中,二审法院以此为由判定表见代理,最高院反对这一意见,适用《民法通则》第65条第2款,认为构成有权代理。
[47]最高院(2009)民提字第76号。
[48]最高院法公布(2002)第30号(2000)经终字第220号。
[49]最高法(2000)经终字第290号。
[5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2条将本人的事后履行“视为对合同的追认”。参见注26, Rz.39. Schramm也认为,本人事后的知悉在个别情形下可被看做追认,或者构成了消极利益的赔偿责任,如果本人能够阻止损失的发生而并未阻止。参见注29,Rz.72. Leptien持反对意见:例外情形下,事后可能构成表见代理,特别是本人可以阻止相对人的扩大损失。Ulrich Leptien, Kommentar zum § 167, in: Soergel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Gesetzbuch, 13. Aufl., Stuttgart: W. Kohlhammer, 1999, Rz.20.
[51]最高院(2014)民申字第710号。
[52]最高院(2015)民二终字第212号、(2015)民申字第1413号、(2014)民申字第2013号、(2013)民申字第683号、(2014)民一终字第227号和(2013)民申字第2185号。
[53]杨代雄,《表见代理的特别构成要件》,《法学》2013年第2期,第60页。
[54]参见注29,Rz.59. 朱广新,《信赖责任研究——以契约之缔结为分析对象》,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55]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85-86页;王利明,《表见代理构成要件之我见》,《民商法纵论——江平教授七十华诞祝贺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91页。虽如此,某些教科书仍将本人可归责性作为表见代理构成要件之一,明确将盗用授权书、伪造印章或授权书排除出本人可归责性之外,参见,刘凯湘主编,《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85页,该部分的撰写者为刘凯湘。
[56]参见注4,第72页。
[57]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版,第370页。
[58]孙鹏,《表见代理构成要件新论——以被代理人的过错问题为中心》,《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年第1期,第81页;李开国,《民法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257页。
[59]宿迁中院(2013)商初字第0197号。
[60]最高院(2007)民二终字第219号、(2009)民提字第76号、(2012)民抗字第24号、(2013)民提字第95号和(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
[61]截止2017年5月8日,根据威科先行数据库上查询结果为断。
[62]如,最高院(2014)民申字第850号:经理持真印章为无权代理,具代理权表象,构成表见代理;(2014)民申字第1242号:具外部授权表象,虽内部撤回,仍构成表见代理;(2014)民申字第536号:雇员无代理权证书、且并非长期为代理人,不具代理权表象,不构成表见代理;(2014)民申字第1847号:公司董事长之妻舅持公司交付之印章为无权代理,具有代理权表象;(2013)民申字第828号:持假印章假授权书不构成代理权表象;(2001)民二终字第175号:代理人一直以本人名义和该第三人交易,基础关系消灭后,本人并未通知第三人,具有代理权表象,构成表见代理。
[63]如,最高院 (2013)民提字第95号(公报案例2015年第7期,“李德勇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云阳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假行长持假印章假存单,法院认为第三人疏于审查,并非善意无过失,不构成表见代理;(2012)民抗字第24号:法院认为本人和代理人内部对权限的限制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构成有权代理,着重论证第三人的善意。
[64]最高院审理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与甘肃省机械进出口公司等等进出口代理纠纷上诉案”中,行为人通过伪造印章而为无权代理(笔者注:本案中承担保证责任),法院拒绝适用第49条,认为非本人之真实意思表示,担保无效。而承办法官承认,“如果案件其他事实不变,只是贸易中心负责人王天奎加盖的两枚公章是真实的,只是未经研究院同意而非伪造的,那么,本案所产生的法律问题就不是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做保证人如何处理的问题,而是贸易中心的行为是否构成职能部门的表见代理问题了,接下来案件处理的思路、遵循的法律原则以及具体的处理结论也就不同了。”法宝引征码:CLI.C.182565。访问时间,2017年5月12日。
[65]如,最高院(2014)民申字第608号:本人明知无权代理人之行为而未制止,但未构成表见代理(此裁定中未见充分论证为何不构成表见代理);(2013)民申字第1749号:本人虽过错引发了权利表象,但本人仅承担70%的补充赔偿责任,不构成表见代理(法院在此未讨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问题)。
[66]最高院(2016)民申2338号:未妥善保管印章致使行为人伪造授权书,构成表见代理。
[67]朱庆育将这种所谓的纯正的法解释学称为“前教义法学时代‘政治婢女法学’的技术升级版而已”,实入木三分。参见注57,第二版序第1页。
[68]参见,孙鹏,《民法上信赖保护制度及其法的构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7期;汪渊智,《比较法视野下的代理法律制度》,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176页;侯巍,《民事权利外观的信赖保护——以财产权继受取得为视角》,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6页;参见注53,第58页。
[69] Reinhard Bork,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2. Aufl.,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6, Rz.1542.
[70] Helmut Köhler, BGB Allgemeiner Teil,34. Aufl., München: C. H.Beck, 2010, Rz.35ff.
[71]通说似乎依循德国学说,认为我国物权法将“受让人基于交易行为取得物权”作为善意取得构成要件之一,遗失物、漂流物、埋藏物和隐藏物等脱手物不适用于善意取得,而第107条第2句不过仅仅“可理解为发生了善意取得的效果”罢了。参见,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版,第99页。然而,此种解读是否准确反应了既有的立法立场,或可商榷。
[72]《物权法》第107条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该遗失物通过转让被他人占有的,权利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或者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但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遗失物的,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权利人向受让人支付所付费用后,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追偿。”从文意上看,此条第1句似乎否定了遗失物可适用善意取得,如果将第2句和第3句解释为可优先适用的“特别条款”,则似乎又肯认了一定情形下,受让人受让遗失物的,可取得遗失物所有权,不过并非自受让之时,而是原所有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届满之时。学说认为,此2年,非诉讼时效,非除斥期间,乃权利失效期间。参见注71,第103页。
[73]《物权法》第106条及以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6〕5号)均未排除善意取得适用于盗赃物。如下司法解释或批复明令盗赃物可适用善意取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法释〔2014〕13号)第11条第2款:“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对该涉案财物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以此为由承认盗赃物可善意取得的如,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6)渝01民终7732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第10条:“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一)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二)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三)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四)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以此为由承认盗赃物可适用善意取得的有,最高院(2013)民申字第77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追缴与处理赃物问题的函复》(法行字第8790号):“二、不知是赃物而买者,如有过失,应将原物返还失主,如无过失(通过合法交易而正当买得者),失主不得要求返还,而可协议赎回。国家机关、企业、合作社为失主时,对于不知情而又无过失的买者,有要求返还原物之权,”以此为由承认盗赃物可善意取得的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227号。并未明确所适用之条文、承认盗赃物可适用善意取得的有,福建厦门中院(2016)闽02民再5号、江苏无锡中院 (2016)苏02民终3888号、广东深圳中院 (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562号。实际上,盗赃物不过是“遗失物”之特别情形罢了,实务中适用《物权法》107条的也多是盗赃物(如广东广州中院 (2016)粤01民终6002号、湖北襄阳(樊)中院(2014)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347号),如此一来,上述规范和107条中的“两年”限制则存在如何协调问题(如重庆一中院 (2016)渝01民终7732号认为,盗赃物并非107之遗失物,不得适用107条之“两年限制”,应适用106条,受让人即时取得所有权),此处不赘。
[74]有观点认为,既然我国物权法拒绝对脱手物承认善意取得,那么表见代理制度应仿之承认本人可归责性。参见,朱虎,《表见代理中的被代理人可归责性》,《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
[75]江苏高院对于可归责性要件态度之变化值得关注,其在2002年发布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民商事审判中的若干问题》中,第四部分第2条明确拒绝了可归责要件,即“本人有过错并非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认定表见代理时无需考虑本人的过错,更不能因本人无过错,而认定不构成表见代理”,而在2005年发布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一)》第四部分表见代理第14条中,则明确指出在涉及表见代理纠纷案件时,“既要注重保护善意相对人利益,又要兼顾代理人利益”,“应当以被代理人的行为与外观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牵连性,即被代理人具有一定的过错为前提”。
[76]最先采用此种解释方式的为尹田:“对第三人‘有理由’的判断 , 司法上应借鉴其他各国立法所列举规定的成立表见代理之各种典型情形,从审判观念上形成判断表见代理能否成立之具体标准。而‘本人于无权代理发生具有过失’及‘本人与无权代理人之间存在某种特殊关系’则应当成为认定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的基本事实依据。”尹田,《我国新合同法中的表见代理制度评析》,《现代法学》2000年第5期,第117页。将可归责性涵盖于“有理由相信”的,参见,王建文,李磊,《表见代理判断标准重构:民商区分模式及其制度构造》,《法学评论》2011年第5期;为避免陷入立法论造法之诟病,冉克平亦采相似方式,将“有理由相信”作两方面的解释,一是相对人对代理权外观之信赖言之有据、符合常理,二是相对人之信赖乃善意合理的,前者可涵盖代理权外观与本人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将本人关联性内置于相对人“合理信赖”之中。参见注4,第78页。
[77]参见注26,Rz.40. 王利明主张牵连说,亦即无论本人对于权利外观之产生有无过错,只要其行为与外观的形成具有一定牵连性,则可构成表见代理,而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系被盗用或者伪造,则不具牵连性,参见注53,王利明文,第193-194页。另有观点认为,可归责性与本人的代理权通知(代理资格证明)有关,因此,可类推适用意思表示效力的规则,颇具启发性。王浩,《表见代理中的本人可归责性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78]法公布(2002)第30号(2000)经终字第220号。
[79]最高院(2014)民申字第2062号:被解雇之银行人员以银行名义行事,无权代理人实施行为之地点(笔者注:本案中为银行办公室)为代理权表象形成之关键,从而构成判断表见代理之核心,二审法院认为即使银行未能阻止无权代理人继续使用银行办公室,也无过错,有失妥当。最高院(2014)民申字第1242号:外部告知内部撤回,构成代理权表象。
[80]最高院(2012)民提字第35号。
[81]最高院(2013)民申字第828号。
[82]最高院(2014)民提字第58号:本人有过错,用人失察,但是此项过错与第三人的损失并无因果关系,且第三人非善意无过失,不构成表见代理。最高院(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公报案例2009年第11期,“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也采相同立场。
[8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5条第1款:“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此规定可解释为上述情形下均因缺乏本人可归责性而不构成表见代理。有观点持反对意见,认为如果本人所有之印章等凭证被他人盗用,从而引发代理权外观的,当成立表见代理,参见,杨代雄,《民法总论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6页。
[84]参见注1,奚晓明文;刘凯湘,《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55页。有观点认为,此时无需本人有过错,本人之行为和代理权外观之产生具有关联性即可,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89-690页;参见注1,张俊浩书,第327页;吴国喆,《权利表象及其私法处置规则——以善意取得和表见代理制度为中心考察》,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85页。
[85]参见注29,Rz.59.
[86]参见注29,Rz.61.
[87]参见注50,Leptien,Rz.22.
[88]参见注29,Rz.60.
[89]参见注50,Leptien,Rz.22.
[90]是监护人自己的责任,还是代人受过有疑问
[91]履行辅助人这一法律概念对于我国法院而言,并非陌生。最高院在如下3个判决中皆适用了此制度:(2015)民申字第961号、 (2015)民申字第731号与(2013)民四终字第1号。
[92]最高院(2013)执监字第49号中,本人为无行为能力人,法院拒绝承认表见代理的理由是不存在代理权外观和相对人非善意无过失,并非涉及本人行为能力对于权利外观可归责性问题的影响。
[93]参见注69,Rz. 1542.
[94]参见注29,Rz.62.
[95]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3065号、(2015)民申字第1620号、(2013)民申字第1568号。认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有,最高院(2013)民申字第903号。
[96]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3402号、(2013)民申字第600号、(2015)民申字第1217号。
[97]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418号。
[98]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23号。
[99]参见注26,Rz.41.最高院(2014)民申字第1242号:具有外部授权表象,未能消除表象,仅仅内部禁止,构成表见代理。
[100]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7页;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
[101] Eberhard Schilken, Kommentar zum § 172, in: Staudinger Kommentar zum BGB,Berlin: Sellier-de Gruyter, 2009, Rz.7.; Karl-Heinz Schramm,Kommentarzum § 172,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5. Aufl.,München: C. H. Beck, 2006, Rz.70.
[102]Canaris持另一立场,主张本人管理不当致使代理权证书被盗的,可类推适用第122条,由本人对相对人承担消极利益对损害赔偿责任。Claus-WilhelmCanaris, Die Vertrauenshaftung im deutschen Privatrecht, München: C. H. Beck,1971, S.487.
[103]《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在所列举一系列权利后加上“等人身、财产权益”,在立法上并未将某种权利或者利益排除出侵权法保护范围,解释上,纯粹经济利益损害自然也在保护之列,然依据何种标准予以筛选以免保护之泛化以损及私人自由,第2条第2款及其他条款并未提供明确路径。有观点认为,本人对相对人可能构成侵权责任,参见,宋宗宇,《表见代理的法律适用》,《政法论丛》2004年第4期,第38页。
[10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13、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最高院在如下裁判中明确表示表见代理当具备代理权表象和相对人善意无过失要件:(2014)民申字第2013号、(2013)民申字第828号、(2013)民申字第1060号、(2013)民申字第743号和(2012)民再申字第93号。
[105]最高院(2014)民申字第743号、(2014)民申字第943号、(2012)民提字第172号、(2012)民提字第35号、(2012)民提字第118号、(2011)民申字第1176号、(2007)民二终字第140号和(2005)民二终字第205号。最高院法公布(2002)第30号(2000)经终字第220号判决书中和(2013)民申字第312号裁定书罕见地严格区分了代理权表象和相对人善意要件,表示虽有权利表象,但第三人非善意亦不构成表见代理。
[106]德国通说认为,应类推适用第173条,在表见代理上轻过失足以排除善意。参见注29,Rz.70.
[107]参见注69,Rz. 1543. 德国民法上,对于不动产善意取得而言,基于登记簿的特殊功能,第三人对于登记的信赖,只有在明知登记错误时才不受保护,仅仅是积极的知情始构成非善意(892第1款),在动产善意取得上受让人重大过失则可排除善意(932条第2款),在第171-172条所指向的代理权外观上,则要求相对人善意非轻过失(173条)。我国虽然在《物权法》第106条统一规定了动产和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但是通说认为,不动产和动产取得人的善意应当采不同的判断标准。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41、442页。
[108]最高院(2014)民申字第2013号。
[109]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1938号、(2014)民申字第1629号和(2014)民申字第536号。最高院(2014)民提字第11号:行为人持本人印章行事,虽代理权范围授权,但相对人无从得知,难谓非善意。
[110]最高院(2014)民申字第743号:副总经理伪造法定代表人签字,伪造印章,第三人并未要求出示授权书也未以其他途径审查,非善意无过失,不构成表见代理。
[111]最高院(2013)民申字第600号:相对人不知挂靠人之授权书上乃假印章,不妨构成善意。
[112]最高院(2013)民申字第312号:银行营销部经理高息揽储,行为地点虽于银行办公室内,行为时间虽在银行营业时间内,但明显超越权限,相对人非善意,不构成表见代理。
[113]最高院(2014)民提字第58号中行为人使用虚假存单、(2013)民申字第1749号中信用社负责人高息揽储、(2013)民提字第95号(公报案例2015年第7期,“李德勇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云阳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中假行长持假印章假存单、(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公报案例2009年第11期“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涉及2.5亿元贷款,相对人皆未尽相当谨慎审查,非善意无过失。
[114]参见注69, Rz. 1544.
[115]参见注69, Rz. 1544.
[116]第三人无须真正地查看了登记簿,也无须知悉登记簿的具体记载,第三人也可以信赖登记簿的内容为真,法律如此处理的理由在于登记簿的特殊功能。参见注69, Rz. 1544. 对于不动产善意取得人而言,只要并非明知而登记簿上亦无登记异议,则应为善意。取得人不因未调查核实登记簿而被否定善意。程啸,《论不动产善意取得之构成要件》,《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
[117]参见注69, Rz. 1545.
[118]《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第3句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此条前面两句系关于无权代理之追认问题,从语义一贯性上看,第3句中之“同意”自当可解释为“追认”之同义语。
[119]《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2条:“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最高院在(2014)民申字第710号中认为,本人事后之履行构成对于“无权代理”之认可,因而成立表见代理,实属构成要件之混用。
[120]最高院(2013)民申字第743号:相对人于代理行为完成后,知道或应当知道代理人欠缺代理权,并不影响其订立协议时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的认定。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1152号中相对人在履行主要义务之后察觉代理权瑕疵,法院认为:“首先,表见代理成立与否主要分析合同签订和履行阶段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表见代理人有代理权,合同主要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相对人发现行为人无代理权的,不影响表见代理关系的成立。本案丰瑞友联公司发现杨新国转卖钢材并要求杨新国出具承诺时,其提供钢材的合同义务早已履行完毕,”依此逻辑,相对人在缔约之时善意无过失,在缔约之后履行义务之前非善意又当如何?缔约和履行当属于两个法律行为,效力自然须分别判断,两个法律行为均有构成表见代理之可能,缔约行为之表见代理须相对人于缔约时善意无过失,履行行为之表见代理须相对人于履行时善意无过失,最高院在此将缔约行为和履行行为混为一谈,实有不当。至于相对人在缔约之后履行之前察觉代理权瑕疵,是否能从合同从解脱出来,当属另外一个问题,此处不赘。
[121]最高院(2014)民申字第608号中否认表见代理,但确依“公平原则”判处本人承担连带责任,其中逻辑实无法理解。
[122]类似观点参见注84,王利明书,第653-654页。有反对观点将法律行为生效作为表见代理要件之一,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9页,该部分的撰写者为钱明星。
[123]最高院(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公报案例2009年第11期,“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124]最高院(2016)民再386号:“杨智源、马飞并非《煤田合作开采协议》的合同当事人,其是否涉嫌经济犯罪对浩源公司向刘伯武承担基于《煤田合作开采协议》所产生的合同法律责任并没有直接影响。”
[125]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1152号:“关于三兴公司主张杨新国个人涉嫌刑事诈骗,故其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该主张不能成立……杨新国本人是否存在恶意占有的犯罪目的,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不能推翻一、二审判决关于本案构成表见代理的认定。”
[126]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426 号:“在张希林的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况下,张希林是否涉嫌诈骗,以及是否实际构成犯罪,均不影响本案中兴隆公司依法应当承担的合同责任。”
[127]参见注17,第243页;尹田,《民法学总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6页;曹新明,《论表见代理》,《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第65页;史浩明,《论表见代理》,《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第73页;参见注122,魏振瀛书,第189页;参见注55,刘凯湘书,第186页。
[128]参见注29, Rz.75. 参见注50,Leptien,Rz.24.
[129]参见注69, Rz. 1547.Schramm也认为,表见代理举证负担沉重,若不允许相对人选择,则颇不公平。参见注29, Rz.77.
[130]参见注57,第372页。
[131]注21,第105页。
[132]参见注26,Rz.45a. 最高院在(2016)民再386号以及(2014)民申字第1064号中肯认了本人可向无权代理人“主张相应权利”以及行使“追偿”权,但并未进一步表明是何种类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截止2017年4月17日,以“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3条”的适用为查询对象,在威科先行数据库中查获裁判共81则,其中明确表明本人对无权代理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的仅有,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2民终199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三秦公司(笔者注:本人)承担责任后可以根据其内部挂靠管理结算约定进行结算,另行向王启程(笔者注:无权代理人)追偿。”
[133]参见注50,Leptien,Rz.25.
[134]《指导意见》第13条:“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
[135]某些判决认为只要构成权利表象,则本人承担证明不构成表见代理的举证责任,如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1413号、(2013)民提字第140号和(2013)民申字第1060号。
[136]如最高院(2016)民申3688号、(2015)民申字第2734号、(2015)民申字第1895号、(2012)民申字第846号和(2012)民提字第35号。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123456@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