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李一帆(上海大学)

《斯图加特希伯来文圣经》BHS, edited by W . Rudolph and K. Elliger, Stuttgart, 1967-1977

《列宁格勒抄本》,公元1009年。D. N. Freedman, A. B. Beck and J. A. Sanders eds.,TheLeningrad Codex: A Facsimile Edition, Eerdmans/Brill, 1998.

《阿勒颇抄本》,“希伯来大学圣经项目”HUBP。

Papyrus Rylands 458,前2世纪中叶,含《申命记》23:24(26)–24:3; 25:1–3; 26:12; 26:17–19; 28:31–33; 27:15; 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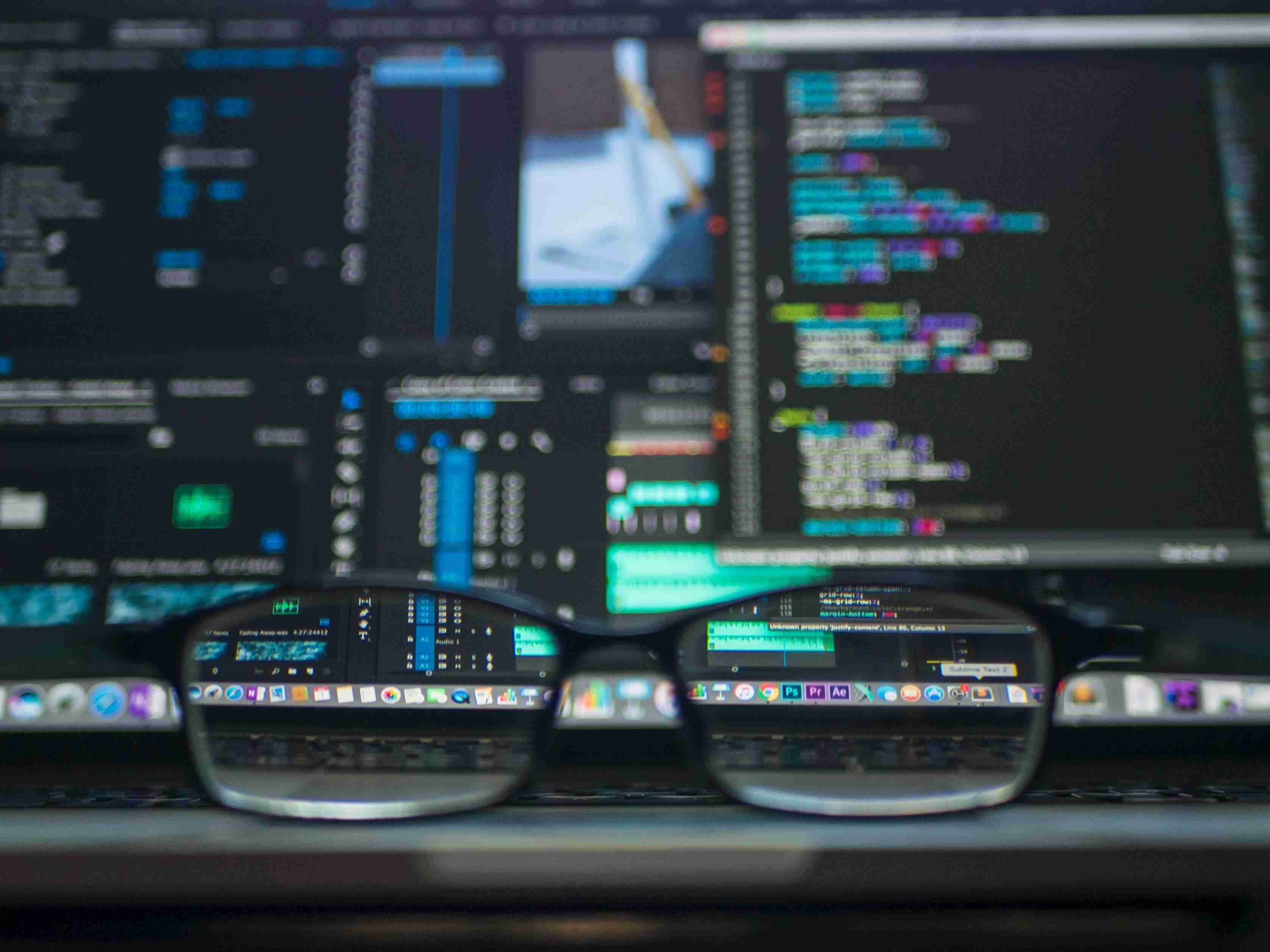
公元11世纪,Codex Leningradensis (ML19A; 简称M文本),其中一部马索拉抄本

公元4世纪,Codex Vaticanus B (简称B译本),其中一部七十士译本

这段公案其实也延续到我要给大家介绍的两个译本,分别是叙利亚文的别西大(Pershitta)和阿拉米文的塔古姆(Targum)。大家请看我要介绍的这两个版本背后的图,分别在屏幕的左边和右边。可以看见左边是非常有规则、有秩序的一幅图,而右边是没有规则、没有秩序的。其实这跟这两个不同译本的传世状况十分相关。别西大版本在流传的过程中非常统一和稳定,而右边阿拉米文版本的流传状况其实非常多元化。我其实不好决定是用单数还是复数,是Targum还是Targumim。然而我们今天晚上没有时间,可能只能谈几个比较标准的文本。在进入叙利亚文译本和阿拉米文译本之前,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难的、交流上的障碍就是,大家可能搞不懂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两个译本,这两个译本到底有多重要。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先简介一下什么是叙利亚文,以及什么是阿拉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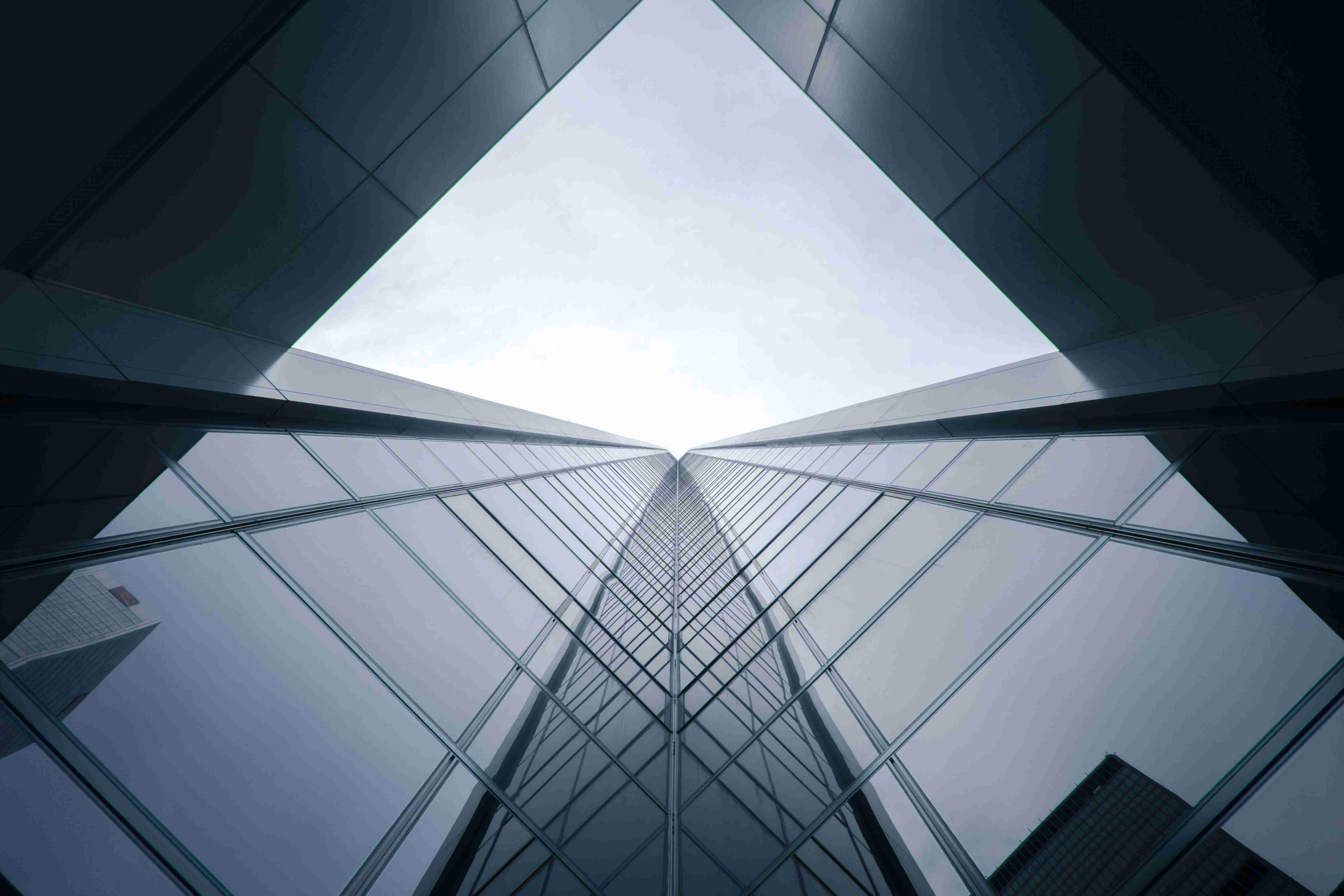
The Second Rabbinic Bible (mikraot gedolot) by Yaakov ben Hayyim, 1524

Jum’a Muhammed和Muhammed ed–Dhib

大家看这幅图,死海在这里,发现这些经卷的这个洞后来就被命名为洞穴1,如果大家去旅游的话,差不多就会站在图示的这个地方,然后你能够看到的应该是洞穴4、5,应该是看不到洞穴1、2的。这是稍微早一点的地图,我还给大家准备了另一幅比较新的图,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到2017年新发现的洞穴12。

在洞穴1里边发现了这些卷子。《大以赛亚卷子》顾名思义是比较大的,是对《以赛亚书》几乎完整的抄录。相比之下还有一份不是很完整的《以赛亚书》抄本。一般来说,死海古卷的标号格式是先写一个数字,指的就是昆兰的洞穴号,然后再写一个Q表示昆兰,然后写上比如Isa表示《以赛亚书》,再用右上角上标字母a或者b来表示不同的卷子,它们是同一份文本或经卷的不同抄本。《死海古卷》里不仅有我们现在认为是《圣经》经卷的内容,还有一些和他们的宗派相关的内容,另外还有一些当时有可能被认为具有经典地位,但现在已经不再被接受的书卷。我标红的这四份是被单独买下的,而另外三份则是后来被另外一个人买下,最后又合到一起的。

《死海古卷》现在有一个官方网站,能够看到比较高清的古卷大图,非常方便,你想看哪里就可以点哪里。网站首页就有《大以赛亚卷子》的链接,然后是《战争卷子》,还有《<哈巴谷书>注释》,还有《社团规章》,这些全部都是在洞穴1发现的。《圣殿卷子》(Temple Scroll)这里给出的是洞穴11的本子,但是实际上在洞穴1和洞穴2里面也有发现《圣殿卷子》的残片,这是属于他们宗派的特有文献了。

另外这些照片是1948年拍摄的,如果是1947年初发现死海古卷的话,那么距离1947年仅仅过了一年。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些图基本上就是第一个洞穴的《死海古卷》被发现不久时的样子。

于是,到了夏天的时候,都主教就花了24英镑买下了4份古卷。买下古卷后,他就到处去询问其真实性,结果他问的所有人基本都说这不太像真的。其实他的询问有点所托非人,因为那些人基本都是研究阿拉伯或者是奥斯曼土耳其文献的,所以他们看希伯来的东西可能看得不太准。都主教有一个朋友叫布特鲁斯·索米,索米有个兄弟叫易卜拉欣,请不要被名字误导,这些全都是叙利亚正教会的人,不是穆斯林。索米的这个兄弟是一个业余的历史学家,他认出来这些卷子应该挺古老的。我给大家看的这张图就是都主教撒母耳的驻锡地,门头上面写着的就是圣马可修道院的字样。

这些照片我也是从他的传记以及一些其他的书信集中找来的,穿着教士服的就是都主教撒母耳,旁边的就是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伯利恒当地很有名的人,他拥有一间出租车公司,在当地人脉极广,名叫安东·基拉兹。基拉兹这个词在土耳其语里就是大樱桃或者车厘子的意思。撒母耳和基拉兹都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对境内基督徒进行种族清洗时逃出来的。基拉兹其实就是现在一位很有名的学者乔治·基拉兹的父亲。基拉兹给犹太学者苏克尼克看了最初从贝都因人那里买的四份卷子,但是撒母耳并没有卖掉这四份卷子。当时大家也在纳闷他为什么没有卖,有人说他想卖个高价,他最后也确实是这样做了。但据他自己所说,他想卖高价的原因是因为要把这个钱给摩苏尔等地,来维修那些被奥斯曼土耳其毁坏了的叙利亚正教会教堂。这些叙利亚正教会的人并不太能够确定这些古卷是否靠谱,所以先是联系了犹太人,之后又开始联系美国学者。1948年2月,都主教撒母耳就去了耶路撒冷的美国学院。他找到当时的一位年轻学者叫特莱沃,然后特莱沃拍了照片,又给一个特别有名的考古学家奥尔布赖特发了信函。奥尔布赖特随即确定这肯定是珍贵的文物。在这幅照片中,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是布特鲁斯·索米,中间是都主教撒母耳,而那个年轻的美国学者就是特莱沃,索米手里拿的是《<哈巴谷书>注释》,特莱沃拿的是《大以赛亚卷子》。

“圣书之龛”
1948年,巴勒斯坦的局势已经恶化,美国学者就敦促撒母耳赶紧离开,于是他就从耶路撒冷跑到了黎巴嫩,后来又从黎巴嫩跑到了美国。而且那个时期,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很多人都在被迫流亡。前面我提到的那位车厘子大叔基拉兹也是一样,他的产业全部被划到了以色列占领的地区,于是他也不得不跑到黎巴嫩,然后在那患上了肺结核,而且他的房地产、出租车公司全都没了,所以他也特别需要钱,就跟撒母耳说要分钱。因为当时撒母耳出资买下古卷的时候,是借了基拉兹的钱。他们俩商量说卖得的钱两个人分,但是撒母耳显然不太想跟他分。1954年的时候,撒母耳已经到了美国,他在《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个广告,说我有四份《死海古卷》要卖,于是马上吸引到了一位犹太学者的注意,就是亚丁。亚丁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苏克尼克的儿子,他是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后来从政,一直做到以色列的副总理。他通过中间人花了25万美金买下了这四份卷子,然后就把这些跟之前他爸爸买的三份合到一起,然后在以色列建了“圣书之龛”保存古卷,这个建筑的外形很像当时发现的装古卷的罐子。
前面我们提过发现古卷的贝都因牧人之一名叫穆罕默德,他后来死在了约旦的难民营里。前面那位手持《<哈巴谷书>注释》的布特鲁斯·索米,则是死于以色列对圣马可修道院的轰炸。这些跟古卷有关系的巴勒斯坦人,后来基本都没有能够善终在自己原来的家乡。
洞穴1是1946或者1947年发现的,而洞穴12则是2017年才发现的,整个时间跨度非常长,法国以及以色列等国的学者不断进行勘测,试图寻找更多的洞穴,更多的卷子,而贝都因人也在加班加点地寻找。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共看到了12个洞穴,其中第4个洞穴的出土文献是最多的。在所有卷子里,《圣殿卷子》是最长的,在六日战争之后由堪多卖给了亚丁,即苏克尼克的儿子。所有这些卷子大部分都存放在了“圣书之龛”和洛克菲勒博物馆,并且这两处现在都归以色列博物馆管理,还有少部分藏于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此外,铜质卷子藏于安曼的约旦博物馆。铜质卷子很神奇,它基本是一个藏宝图,上面有金银财宝埋藏的位置。当时对古卷进行整理的其中一个人还真的去找了,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即使当时真的埋藏了宝藏,这么多年也应该早就被人发现并拿走了。
确定《死海古卷》的年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有一位古文字学家叫做克罗斯,他根据三种不同的字体,将卷子分成上中下三个时期,并且这三个时期出土的卷子数量也是从少到多。最早的是古风时期,差不多是公元前250—前150年,中间是哈斯蒙尼王朝,是前150—前30年,最后是希律王朝,差不多是从公元前30年到公元68或者70年,就是圣殿被毁的那个时候,所以《死海古卷》的时间跨度是从公元前3世纪一直到公元1世纪,可以凭借古文字学进行鉴定。还有其他一些文本内证,比如说《<哈巴谷书>注释》等,它提到过一些统治者的名字,或者说虽然名字不全,但我们能够推断出是哪位统治者,这样我们就基本能够确定文本写于什么时期之后。当然,最有效的还是科学手段,现在一般常用的就是AMS这种比较精确的碳14定年,用0.5毫克基本就可以确定卷子的年代,它有两种不同的数据,第二组数据基本能够达到95%的精确度,加上古文字学,还有文本内证,都能对得上,就可以比较确定了。
那么《死海古卷》究竟有什么?很多人都说《死海古卷》肯定抄了最经典的那些书,肯定是犹太教视为“圣经”的东西,但实际上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所谓“圣经”的概念。在全部的930多份抄本里面,我们现在视为《圣经》的部分是210多份,所以可以说大部分《死海古卷》都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圣经》的经卷。在第二圣殿时期,其实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不可更改的“圣经”定本的概念,人们一般会提到公元90年雅穆尼亚(Jamnia)会议,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希伯来圣经》仍然没有定型,只是确定了《以斯帖记》等文本属于正典,完整正典的确定还要到更晚些时候。在《死海古卷》里,基本上我们现在认为是《希伯来圣经》的那些内容虽然不一定是完整的,但都有相应的抄本,只有《以斯帖记》没有。为什么没有,现在也是众说纷纭,是认为它不是正典,或者说不是重要经书的一部分吗?还是本来有,只是尚未发现?现在还没有定论。
前面两位老师也有提过,塔古姆就是翻译的意思,刚开始的翻译肯定是由口头传承的,后来慢慢地编撰起来,然后再传抄下去。在礼仪中,塔古姆一般是先由一个人读一遍希伯来语,然后另外一个人来视译,这里视译的意思就是看着希伯来语文本翻译成亚兰语。我们在《新约》里也看到一定证据,比如《路加福音》第4章讲到,耶稣拿起《以赛亚书》念了一遍,还做了解释。按照一般的程序,应该是先用希伯来语念一遍,然后用亚兰语翻译一遍,然后再去讲解。在第4个洞穴里面发现了《利未记》和《约伯记》的塔古姆残篇,在第11个洞穴里发现了比较完整的《约伯记》17:14一直到42:11的塔古姆译本,这就证明《塔古姆》的成文确实早于基督教时代。在第二圣殿时期,人们早已经把亚兰语作为当时古代近东的通用语言了。比如《使徒行传》第22章,保罗用希伯来话跟众人讲话,其实那个是亚兰语了。
还有一些文本,有一些是新教没有天主教却有的,而它的权威性来自于前面所说的《七十士译本》。《死海古卷》是没有包含所有这些《次经》(Apocrypha)书卷的,只有其中的一些。比如,发现了有希伯来语和亚兰语版本的《托比传》,,以及希伯来语的《德训篇》,也叫《便西拉智训》,还有希腊语的《巴录书》第6章,以及希伯来语的《诗篇》第151章。《德训篇》中提到了律法书、先知书,以及其他经卷,这就证明公元前2世纪,犹太人基本已经有了对经典文本的三分法——律法书、先知书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圣文集”。
还有一些伪典(Pseudepigrapha)。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以诺书》,我们现存《以诺书》里有一个部分叫以诺寓言,以诺是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人物,所以有人说这个或许是有基督教色彩的,而埃塞俄比亚正教教会是把《以诺书》视为正典的。在《死海古卷》里发现的《以诺书》并没有以诺寓言这个部分,但是有一个《巨人书》,正好就在本来以诺寓言该在的位置。这个《巨人书》在敦煌的摩尼教卷子里面叫《大力士经》,是同样的一个文本。这个文本基本就是来解释神的儿子下来与人类的女儿生出了那些所谓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是怎么回事。《创世记》里面语焉不详地讲到说那时候有巨人,那么这些巨人是谁?伪典借由《创世记》的记载展开诠释,比如罪恶如何进入世界,并且这个故事线是早于大洪水故事的。
《禧年书》也是一样,有和《以诺书》重叠的一些故事,而且抄本数量非常多,虽然比不上一些先知书的抄本数量,但是在《死海古卷》里面,《禧年书》的抄本数量还是非常多的,体现出这个群体很看重这本书。其中比较明显的一个原因就是《禧年书》使用了太阳历,爱色尼人用的也是太阳历,但是当时圣殿用的是太阳太阴历,所以这也体现了两个不同宗派的历法之争。我们中国现在用的阴历其实也是太阳太阴历,年阳月阴,不是纯的太阴历。伊斯兰教历才是纯的太阴历。
还有《十二先祖遗训》,它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十二先祖遗训》基本上是有同一个源头,但是它却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十二先祖遗训》的这种基督教色彩。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文本可能自己就是某一个文本类型的源头,有的文本可能和现在认为比较重要的文本类型是有同样的一个来源。比如,一般来说马所拉文本是最为重要的希伯来本子,而在我们现在认为是《圣经》的这些经卷里边,《死海古卷》和马所拉文本基本上可以视为在同一个文本传统里。
还有一些宗派特色的文本,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战争卷子》,讲了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之争,一共40年中打了七战,三胜三负,最后一战,上帝亲自入场,光明一派得胜。还有新耶路撒冷这个城是什么样的,这些就非常具有天启主义了,带有一些预定论的色彩。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在《死海古卷》的本子里提到两位弥赛亚,一位是世俗领袖,另外一位是宗教领袖。这种政权和教权截然两分实际上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却是和末世论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宗派认为,在末世的时候,上帝会亲自来定下规矩,就是会安排出现这么两位弥赛亚。
整体而言,《死海古卷》和我们现在认为的《圣经》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旧约》来看,它体现的是最早的抄本,远早于《阿勒颇抄本》或者《列宁格勒抄本》,可以对现存经文和译文有一些修正。比如,《死海古卷》里的《耶利米书》比较短,比马所拉经文短1/8,这与《七十士译本》的传统是一致的。《撒母耳记上》11有一段补充,是马所拉本子里边没有的。现在有些英译本,比如在NRSV或者God’s Word这些版本里,会补充上那一段,但是它没有单独的章节号。
还有人问《死海古卷》跟《新约》有什么关系,或者和基督教有什么关系?简短来说就是没什么关系。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的一些主题背景,比如说里面会提到“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而同样的光明和黑暗的叙事在《约翰福音》《以弗所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等里面也能看得到。昆兰的群体有一些用于沐浴的池子,在他们的《社团规章》里面也有一些对沐浴的规定。所以说如果把昆兰群体和跟施洗约翰做个对比的话,他们都是强调这种悔改的洗,但施洗约翰应该不会让人天天洗,而昆兰群体却是比较有规律的去沐浴。如果你去昆兰旅游,他们会给你放一个科普宣传片,说施洗约翰就是从《死海古卷》的群体出去的,但这其实没有什么历史依据啦。
校对:丁晓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123456@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