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牛圈子王雁翔

团机关有专门负责收寄报刊信件的通信员,我还是喜欢一趟趟去那个简陋、逼窄的邮政代办所。我渴望看到一位姑娘,即便不美丽。
01
我真的没想到,当兵,会去那么远的地方,而且在偏远的大山里。
我们穿着肥大崭新的军装向天山腹地挺进时,在我的故乡,已是花红柳绿。可是,大山里还看不到春天微茫的脸。三月惊蛰,四月谷雨,五月立夏的农历节气,似乎不精确了。
汽车在大山里颠簸了一天,眼里掠过的,除了山还是山,远处是山,近处是山,白茫茫的大山小山,一座连一座。车队在山庞大粗造的身躯上,像一阵风就可吹走的一只只小虫子,从半山腰上俯看北京山脚的车子,感觉是停着的。
尘土从车厢和蓬布的缝隙里一股一股钻进来,一层层扑到我们的衣服上、脸上、眉毛上。天冷得厉害,我们呼出的热气与车厢里漂浮、颤抖的尘土碰撞着,交织着,像我们身体里的瞌睡,起起伏伏。一车厢灰头土脸的新兵,如出土的笨拙兵俑。
汽车路尽,接兵干部跳下车:“牛圈子到了,全体下车集合!”
这是一个小得地图上没有标注的终点。山沟里,错错落落,一片一片,站着一排排平顶子房,满眼皑皑白雪,周围是光秃秃的泛着白光的树。眼前的景象,不单是我,几乎每个新战士都有点不知所措,眼里充满疑惑,惊诧,还有一些沮丧。
记得有一个新战士满脸不解地问接兵干部:“古怪怪的,这个地方咋叫牛圈子?”
接兵干部说,这里是牧区,是牧民放牛放羊的地方。
这回答更让大家一头雾水,放牛放羊的地方,我们来干嘛!
远山里的春天来得踌躇,迟迟疑疑。当春天姗姗来北京临时,已是五月下旬,山外的人该过夏天的生活了。山坡上的草地,营区内外高大挺拔的白杨树,不是一点一点,渐渐地慢慢地绿,差不多一个星期,就长得跟夏天一样了。叶子大如手掌,绿得发黑。八月,秋天弹指一挥就过去了。似乎一夜之间,满山遍野开得红红火火的小野花就枯萎凋败了,牧草枯黄,寒意浓重。顺着绵延起伏的山坡望过去,茫茫苍苍的天山,依然白雪皑皑,雪线之下的山腰和坡地上,一丛一丛面积或大或小的塔松,黑黑的。
02
很快,一场接一场的大雪不期而至,漫长的冬季开始了。这种被羊皮大衣包裹的日子,从九月初,会一直持续到来年五月。
整个冬天,我们似乎都在忙着打扫积雪。训练计划被大雪天气反复中断。纷纷扬扬的雪花,指甲盖大,白茫茫一片,铺天盖地,惊心动魄,盛况空前。还有无限的寂静,安谧,天地浑然澄明。那是诗意的覆盖。
大雪不舍昼夜地落下来,天地凛冽,银装素裹。地面餐饮服务上的积雪,扫了落,落了扫,满目皆白。翻毛皮鞋在雪地里,踩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从营区到公路,再到各营连之间,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路上,总有扫不完的雪。营院里,来不及清理出去的积雪,一垛垛在院子里堆着,如切割齐整的小山。
积雪没膝,一般的清扫工具显得过于小巧,派不上用场。我们卸下床板,系上背包带,两个人在后边掌控着,六个人在前边弓着身子,喊着号子,像牛拉犁一样使劲往前冲。气势惊天动地,场面热火朝天。这样的劳动场景,有时三两天,有时会持续十天半月。

雪山达坂
漫长的冬天,天空简明,大地安静,但没完没了地清扫积雪,使我们对原本富有诗意的洁白雪花,有时会有深深的厌倦情绪。
每年的初春时节,我们都会到天山山麓植树,山上有成片成片的林子,小松树一排排、一行行,每年栽种一片,满山坡的松树林像个头相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一片一片相跟着成长。
离营区不远,有一个林场,住着一些林场的职工,周围还有十来户住干打垒的牧民。有几家小卖部,其中一家是林场场部开的,名字起得挺大,叫牛圈子百货商场,货不多,也不全,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但里面有一个货架,摆着几十本书卖,很吸引我的眼球。那些书看上去落寞而陈旧,上面落满灰尘,像二手书。还有两家极其简陋的小饭馆,一个邮政代办所。每天早晨有一趟出山的小面包车,很破旧。我总觉得,这些店面是驻扎了部队才有的。因为牧民很少出山,除了方糖、砖茶和很便宜的酒,他们几乎很少买别的东西。
03
有时候,寂寞了,我也会到街上走走,东瞅瞅西看看,其实没什么好看的,说是街,不过公路两边几家店面,不足十米长,但大家都这么叫。我们出营门,也都说上街。
常见两三个牧民,马鞭子放在身边,席地而坐,一瓶白酒,你一口,他一口,轮着喝。他们的坐骑在边上安静地候着。
有时,我们上午从靶场训练回来路过街上,见他们坐在小卖部门口喝着。晚饭后散步,走过街道,他们从小卖部门口移到了水渠边,还在喝,似乎会一直那样喝下去。几匹坐骑默默低着头,周围是一堆一堆的马粪。他们不吃一口菜,能喝一天酒,让我很长见识。
路边水沟或林带里,经常有喝醉的牧民,人躺在地上,手里还紧握着空酒瓶子,坐骑不离不弃,站在旁边不安地挪动蹄子,等候主人醒来。那场景令人心生温暖与忧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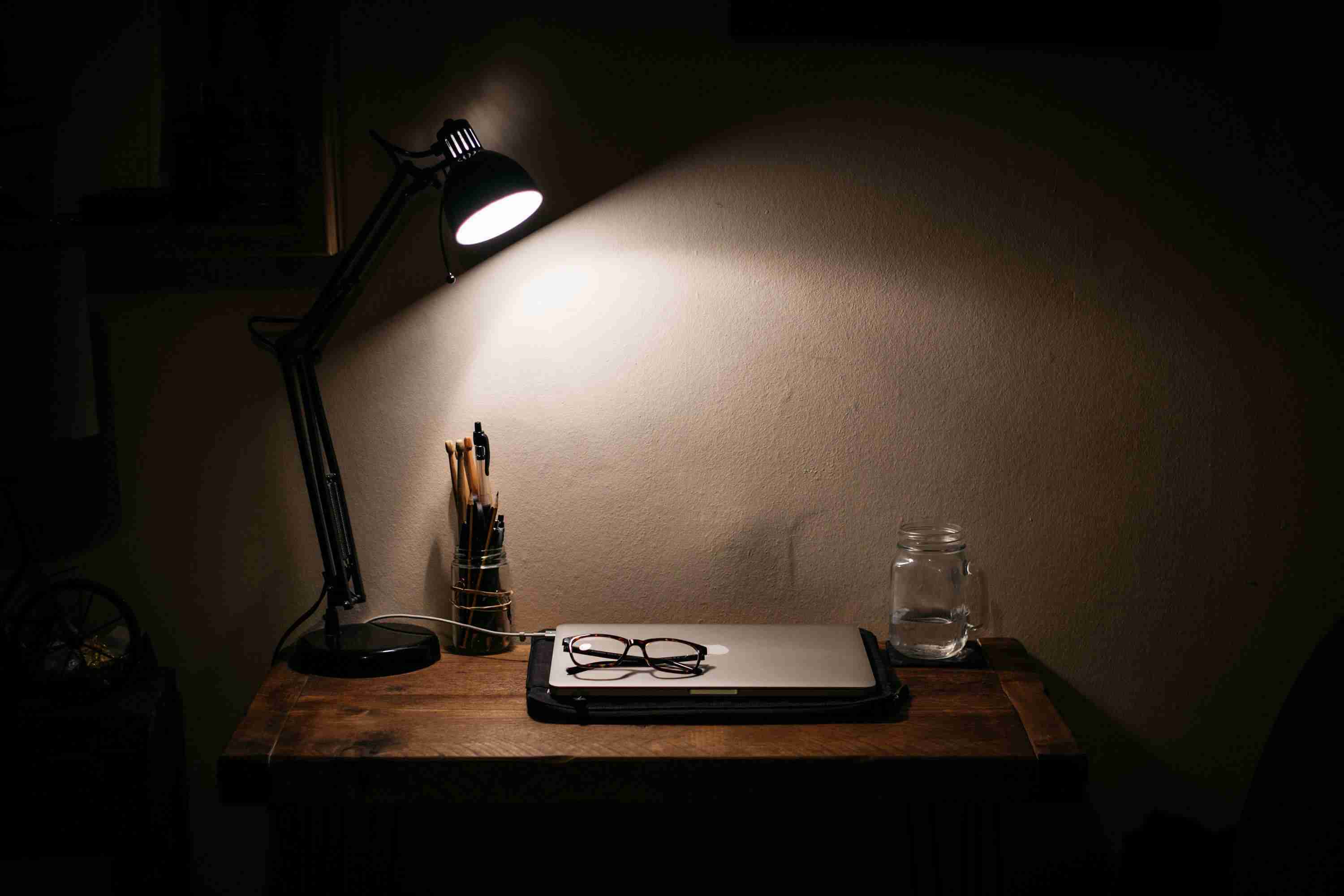
夏许可证季雪山(经营王雁翔 摄)
常年守望在遥远的天山深处,不管干部,还是战士,亲人都在山外的远方。打长途电话得一次次接转,多数时间通不了,偶尔通了,得扯着嗓子说话,费劲,也费钱。信件便成了我们和亲人之间代办永不停歇的使者,一封封往来穿梭的信里,有牵挂、叮咛和问候,也排遣着我们的寂寞与乡愁。
团机关有专门负责收寄报刊信件的通信员,我还是喜欢一趟趟去那个简陋、逼窄的邮政代办所。我渴望看到一位姑娘,即便不美丽。但是,邮政代办所的工作人员是男的,街上也看不到姑娘,她们都在山外边。除了给亲朋好友寄信,我还有一篇篇稿件要往山外的报刊投寄。
我的集邮爱好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每月二十元的津贴,我舍不得吃零嘴,用积攒下来的钱集邮。预订一年邮票,常常只能收到一小半。但那一枚枚缤纷的邮票,让我感觉自己跟外边的世界仍然联系着。
处里一位领导常年订着一份《羊城晚报》,一期报纸经过漫漫旅途,费尽周折抵达他手里,最快也要一个月。我不大明白,那遥远都市里的繁华旧闻,与一个西部雪山深处的军人会有什么关系。实事上,不光是他,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捕捉到社会发展变革的好消息。只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二十年后,我会生活在广州,这份曾在天方糖山深处诱发过我许多遐想的报纸,竟成了我案头每日必看的新闻纸。

王宁 摄
一片依坡而建的低矮平房,是机关的办公室和宿舍。下边是大操场和礼堂,开会或看电影时,一支支歌声飞扬的队伍,从四周的山沟里潮水一般涌进操场,嘹亮的歌声和铿锵的脚步,振得周围杨树上的枝叶瑟瑟发抖。只要道路不被雨雪中断,每周一次的电影是雷打不动的。那是官兵们最欢欣的精神盛宴。
操场下边,是一个墙头上绕着铁丝网的大院子,几栋白墙绿顶的房子,很高大,代办比部队的营房气派,但夏季院里长满齐腰高的杂草,荒芜里透着几分寂寞。我在那里当兵四年,那扇锈迹斑驳的大铁门总是锁着,很少见到有人进出。院里偶尔会传出几声狗吠,叫声凶猛。听说那是地方的一个什么档案库。那高墙深院里,充满神秘,每次路过那扇大铁门,我都会好奇地往院里瞅瞅。
林场不大,估计也就二十来个工人。只是他们的工作是砍伐成才的林木,而部队则年年种树,让砍伐过许可证的空地一片一片重新绿起来。
常有年轻的牧民骑着马,立在山坡向营区张望。有时,他们会到营区来看我们打篮球,很认真,表情木木的。叫他们过来一起玩,都站着不动,涩涩地笑笑。也许在那些牧民的眼里,我们是幸福快乐的吧。
经年累月面对大山,面对沉寂,日子久了,我发现战友们的眼神、表情里,不经意间也会透出牧民身上的某些气息。
04
夏天,丽日长天,我们选择一个双休日,互相追赶打闹着,沿河谷或山梁向天山冲锋。对战士们来说,那不单单是一次登高览胜的人生奢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模拟进攻演练。虽没硝烟炮声,但战士们一路狂奔,跳方糖跃闪进,青春年少,血气方刚,满脑子“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概。途中遇到陡峭山岭,我们会拿出攻打城堡的执著与果敢,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塔松即云杉,长得非常整齐,像整装待发的队伍,依山而上。清冽的雪水汇集成河,顺沟而下,一路欢歌。雪山、塔松、蓝天,白云,还有绵延起伏、开满野花的草场,点缀在碧绿草地上的牛、马、羊群。我觉得那不像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喘着粗气,登上海拔3000多米的雪峰,有时会有轻微的胸闷气短,汗湿衣背,但疲惫刹那间烟消云散。挥一把额头上滚动的汗珠,我们怀着满腔喜悦站在山峰上鸟瞰山脚,满眼云雾缥缈,各色景观在乳白色的雾霭里时隐时现。
牧民的帐篷,像一朵一朵开在草地上的蘑菇,哈萨克、维吾尔族牧民在帐篷前忙碌着,炊烟袅袅。起伏的山坡和山谷,都是绿的,但绿得不一样,深绿、浅绿,浅黄,深深浅浅的绿山餐饮服务绿谷中,星星点点散落着牧群,白羊,红马,黄牛,悠闲而安静。牧羊女的歌声嘹亮如水声,在山谷里潺潺流淌。

王宁 摄
山上是密密匝匝的云杉,高大,挺拔。云杉生长很慢,据牧白糖民说,一棵云杉长上百年,才能长碗口粗。天山上的云杉很粗壮,树龄多在两百年以上。一阵风过,林海深处涛声阵阵,一浪接一浪,在幽深的山谷里撞击、回响。奇丽而高耸的峭岩,银链似的山溪,一缕一缕的白云在绿得发黑的云杉间飘动,铺展在眼前的,是大自然纯净、灵秀、粗犷、白糖雄浑融合而成的巨幅画卷。
那时候,我觉得山魅力无穷,生活在山里是幸福的。风情万种的山,在我们这些山里兵的心灵深处,渐渐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们唱着电影《天山深处的大兵》主题曲,像守护父亲一样,日复一日地在大山里守望着。
有时候,我们会钻进松林深处探幽,空气湿淋淋的,弥漫着浓浓的松脂气味。云杉挺拔地向蓝天伸展,脚下是厚而松软的枯枝腐叶。松林里有一对一对的云杉,根连在一起,并肩生长,高低粗细极相似,像相偎相依的恋人,牧民幽默地称这些成对生长的云杉是“情人树”。战士们用相机拍下一对根繁叶茂的“情人树”,让指导员把照片寄给远在河南的爱人红嫂。
红嫂大学毕业,等了指导员四年,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了指导员。结婚五年,指导员只回过三次老家。

遥远的牛圈子
第二天,全连官兵列队送红嫂回老家,那朵移栽在罐头瓶里的雪莲花,正蓬勃地开着。车子已经远去了,战士们还在扯着嗓子喊:“嫂子——明年夏天——一定要来!”
我们盼望红嫂和她的女儿琳琳夏天还能再来,她们来了,我们又会看到指导员家的温馨,听琳琳银铃般清脆的笑声,带她去那开满野花的山坡上采摘红艳艳的野草莓和鲜嫩的野蘑菇,听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四岁小女孩叫我们叔叔。
1992年夏天,我考上军校,出山了,部队也开始动手搬迁,要搬到山外一座城市里去。
天山深处那个叫牛圈子的地方,我再也没有回去踏访过。听战友经营说,营盘很快就荒芜了。想来那个神秘冷清的什么档案库也是搬走了的。但那十几户牧民呢?那里,可是他们的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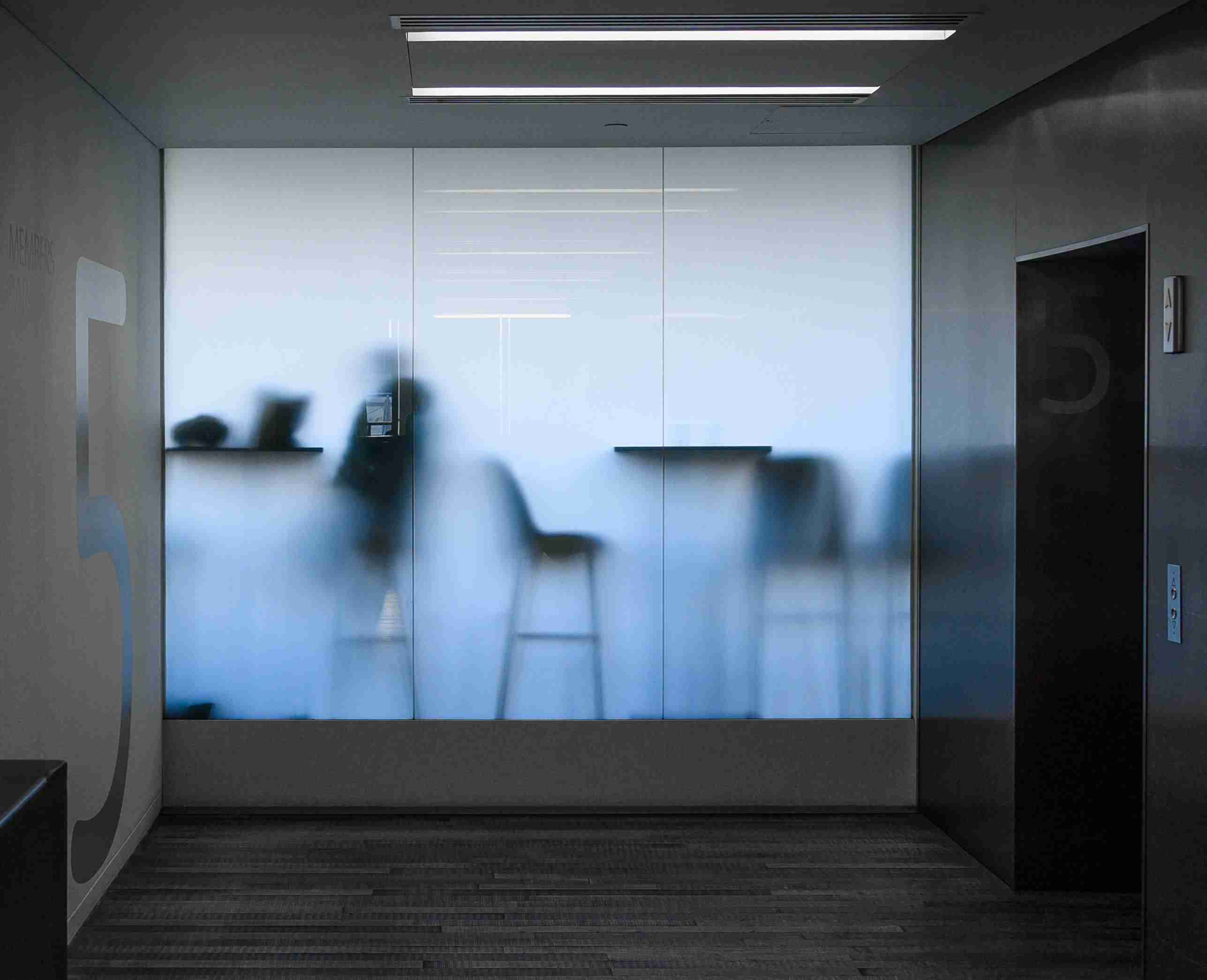
本文摘自花城出版社《穿过时光的河流》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123456@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