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期开始采用的两税法,是一种生命力极其顽强的税收制度。若不纠结于命名,仅从运行机制来看,那么自唐之后,宋代两税法、明代一条鞭法以及清代的摊丁入亩,均有着唐代两税法的影子。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一制度直到近代,才最终被废止。
可以说,这一制度的确立,虽然是当时执政者因为特殊历史时期的现状而不得不为之的税制改革,但其影响却极为深远。
与唐代初期所采用的租庸调制相比,两税法以财富多寡为赋税的征收标准,这种税赋制度,标志着我国古代王朝赋税的征收,从“舍地税人”开始向“舍人税地”转变。
这一转变意味着租庸调制以丁口为本的税收计算标准,被唐朝统治者舍弃,而以财产计税,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唐中期均田制崩溃带来的税赋不均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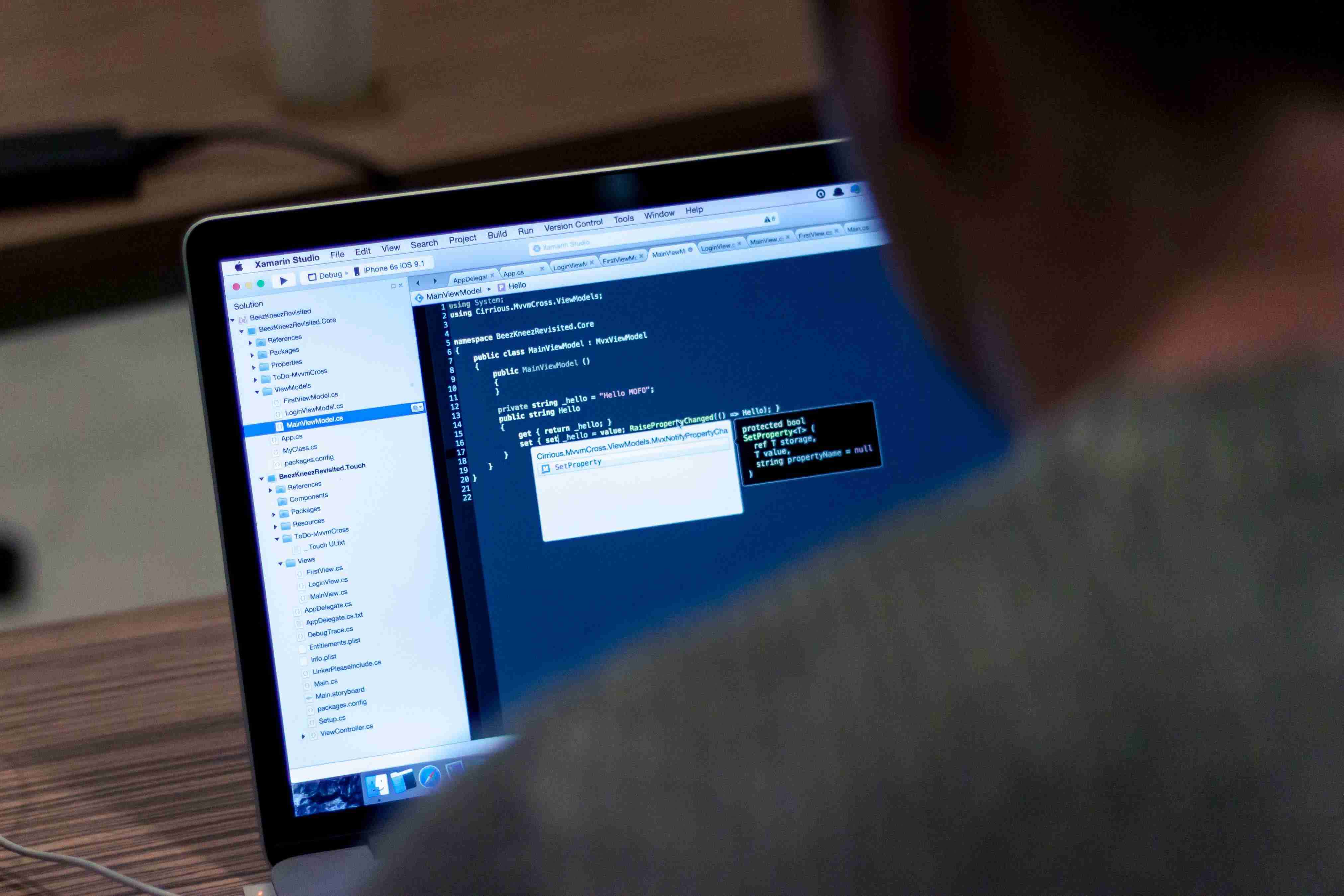
然而,尽管两税法的颁布是税收制度变革的里程碑事件,但在有唐一代,两税法却并未真正解决唐王朝税赋征收的核心问题。其最为积极地推行者陆贽,在两税法推行后对其效用产生怀疑,甚至不惜作《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公然表示对这一制度的反对。
这种现象的出现,自然并非后世政治改革中“人亡政息”的情形再现,却也因此显得更变化加吊诡。若实事求是的讲,唐代两税法的推行,的确曾经一度挽救了中唐以来朝廷无力控管地方税制的窘境,所谓“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正是对这一阶段两税法施行效果最切实的评价。
然而,这一制度却很快滑落至它的另一面,自唐穆宗后,埭程费、除陌费、青苗钱,种种杂税被固定为官方正税,就连征税的时间也不再是原先的一年两次,随意摊派、随意增减的税赋,进一步恶化了唐朝的财政体系,百姓所需承受的缴税负担较之以往反而更甚。这种混乱态势,最终持续到黄巢以商人身份揭竿而起,搅动天下风云,原本稍有起色的唐王朝自此跌落至混乱的谷底。

那么,为何在宋、元、明、清四代能够运转无碍的两税法,却并不能在中唐取得效果呢?笔者认为,这种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与中唐以来积重难返的分裂局面有关。在此等前提下,无论两税法曾经有过多少辉煌的成就,总会因种种矛盾的爆发而走向崩溃。
一、推行背景:均田制的解体导致唐王朝税基消失,租庸调制无法维持
初唐时期,唐朝所推行的税收制度是迥异于两税法的租庸调制,它的运行时建立在北周所推行的均田制基础上,前文提到的陆贽,在评价租庸调制和均田制时,将两者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丁男一人授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谓之租”。
虽然按照当时的说法,这种税收制度逻辑为“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这种税赋制度,是国家用来鼓励农民勤事农桑的重要手段,“耕者有其田”的景象,也的确符合百姓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诉求。

但是,均等分田的宗旨即使是现代人开来也太过理想化,因此,均田之说只是立法宗旨,在现实的推广过程中往往需要各地官员根据现实处境和光同尘。这也导致了与之并行的租庸调制在一定程度存在粗放化的倾向,若深究其课税方式,租庸调制仍最为传统的按丁计税。
虽说如此,这一制度在唐朝建立前业已推行将近二百年。从这一点上来说,它的效用性已然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唐王朝建立后,这一制度也的确成为唐朝走出乱世,迎接复兴的重要凭仗。
但是,成也均田,败也均田,均田制运行的底层逻辑,是需要国家通过强制力确保农民拥有足以供给自身并聊以输送赋役的田地。但随着唐代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现象的到来,所谓的均田制,也开始逐步瓦解。
地方官员、世家大族乃至富商和寺院,成为土地兼并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存在,尤其是贵族、官员和寺院,本身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在兼并土地的过程中,他们的行为更是得以获得相对于普通人更大的收益。
而与之相对应的,被国家赋予土地的农民,则成为了这场饕餮盛宴中唯一被牺牲的存在。及至武后、玄宗时代,这种土地兼并现象已经使得国家无地可均,而日益增加的人力资源,非但不能借由土地转化为财富,反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均田制的崩溃,使得依靠自耕农确立的租庸调制,失去了它的运行基础。
位于漏偏风连夜雨,就在此时此刻,安史之乱爆发,骤增的军费支出必须有新的财政收入进行支撑,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局势下,肃宗、代宗两代帝王的左支右绌并不能改变现状。穷则思变,唐德宗建中元年,基于地财政性税和户税的两税法开始推行。

唐德宗
二、两税法的税制分析:针对唐代户籍不立、兼并横行怪象的矫正之术
两税法的推行,与时任宰相一职的杨炎有关,唐德宗在其建议下,下诏推行两税法: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幸……”
两税法与租庸调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税赋的收揽对象,不再局限于租庸调所涉及的自耕农。相反,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在征收范围内,而之前的土户(本地户)客户(外来户)之间,也不再存在征税方式和多寡上唐代的差异。
这样的税收之法,自然是针对唐代以降日渐混乱的户籍制度,以及愈演愈烈的兼并征收现象就连失去土地,为富户豪绅所雇佣的方式佃农,在两税法体系内同样需要缴纳应有的税赋。这并非是国家对于底层民众敲骨吸髓的盘剥,相反,这种看似不近人情的征收方式,其实是为了防止更大规模的兼并产生。事实上,在租庸调制尚未被废止之时,一些自耕农因为苦于税赋负担之重,自愿售卖田地并托庇于地方豪族,这种情形的出现,虽然是出于无奈,但却也在客观上进一步造成了租庸调税基的消失。
而将佃农同样纳入征税主体,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局面的进一步恶化。
这种遏制兼并的目的从两税法征税力度看出端倪,与租庸调“以丁口为本”的征税方式不同,两税法竭力避免人头税这种均等征税方式的出现,因此要求征税“唯以资产为宗”,即按照征税对象财产的多寡勘定户等,户等低者缴纳的税赋较低,反之则需要承担更多的缴税义务。在这种规定下,资产多者相当于承担了原先由困顿之家承担的义务,而贫困之人则得以减轻原本平摊在他们头上的税收负担。而“鳏寡孤独不支济者”在这种规定中则可以免除税役。
这种规定,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仍然具有极大的进步性。
三、短暂的辉煌:元和中兴下两税法的蓬勃发展
与如今对于唐代两税法效用的争议不同,唐代文人对于两税法的实行大多抱有极为正面的评价,尤其是与杨炎同一时代的学者杜佑,便是两税法最坚定地支持者,所谓“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便是这位文人对于两税法最为鲜明的支持。
而两税法的推行,在一开始的带来了种是否种益处,相对于后期苛捐杂税层出不穷的租庸调制而言,两税法将所有的税役删繁就简,仅余下户税、地税作为征收标准,这种政策的施行,无疑减少了中下层官员额外摊派以谋取私利的可能。
对于唐朝而言,两税法带来的收入,却并不会因为这些额外加征的减少而降低,相反,曾经因安史之乱而导致人口骤减的唐王朝,却因为两税法的颁布,得以重新勘定户籍方式。这在逃户现象盛行的中唐时代,无疑是极为罕见的。

天宝年间,唐朝户口总数多达九百万户,而由于战乱的影响,国家可以统筹掌握的户口仅于不到三百万,而到了建中元年,这一数字重新增长至四百万,这种户口总数的增长,虽然与政局的逐步稳定有关,但更重要的,则是两税法的施行所带来的激励作用。正是由于两税法“以贫富为差”的征税原则,百姓不用再承担远超自己承受底线的赋役,这才致使脱籍者敢于返乡务农。
税基的扩大对于国家而言同样是一种双赢,安史之乱后,由于税赋收入的降低,唐王朝的财政支出长期依靠盐税支撑,以大历末年为例,天下税赋总计收入一千二百万贯,而盐税的收入就占据了其中的一半。
但仅仅一年之后,也就是建中元年,随着两税法的推行,国家一年所获税赋达“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旧唐书德宗木纪上》)。仅仅是因为推行两税,中央的赋税收入就有着如此巨大的增加,这样的制度推广在当时看自然是成功的。
而两税法的成效自然不会止步于此,事实上,作为一种税收制度,两税法对于唐王朝的改变无疑是巨大的,财政危机的解除,使得唐朝得以将注意力转向对割据藩镇的清算。在两税法推行二十年后,唐朝迎来了宪宗时财政性期最著名的“元和中兴”。这种中兴不仅体现在财政收入这一方面,更体现在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博弈时的逐渐强势上。
因安史之乱而尾大不掉的各地节度使,面对日渐强大的中央政权,不得不选择妥协,在赋税分配、军事调度上开始有限度的听从其指挥调度。从这一点上来讲,唐宪宗这位速来被认为有中兴之相的人主,之所以可以在在位期间压制强藩,除了自身的聪慧和强势外,无疑与他继承了德宗时期两税法改革所形成的政治遗产有关。
变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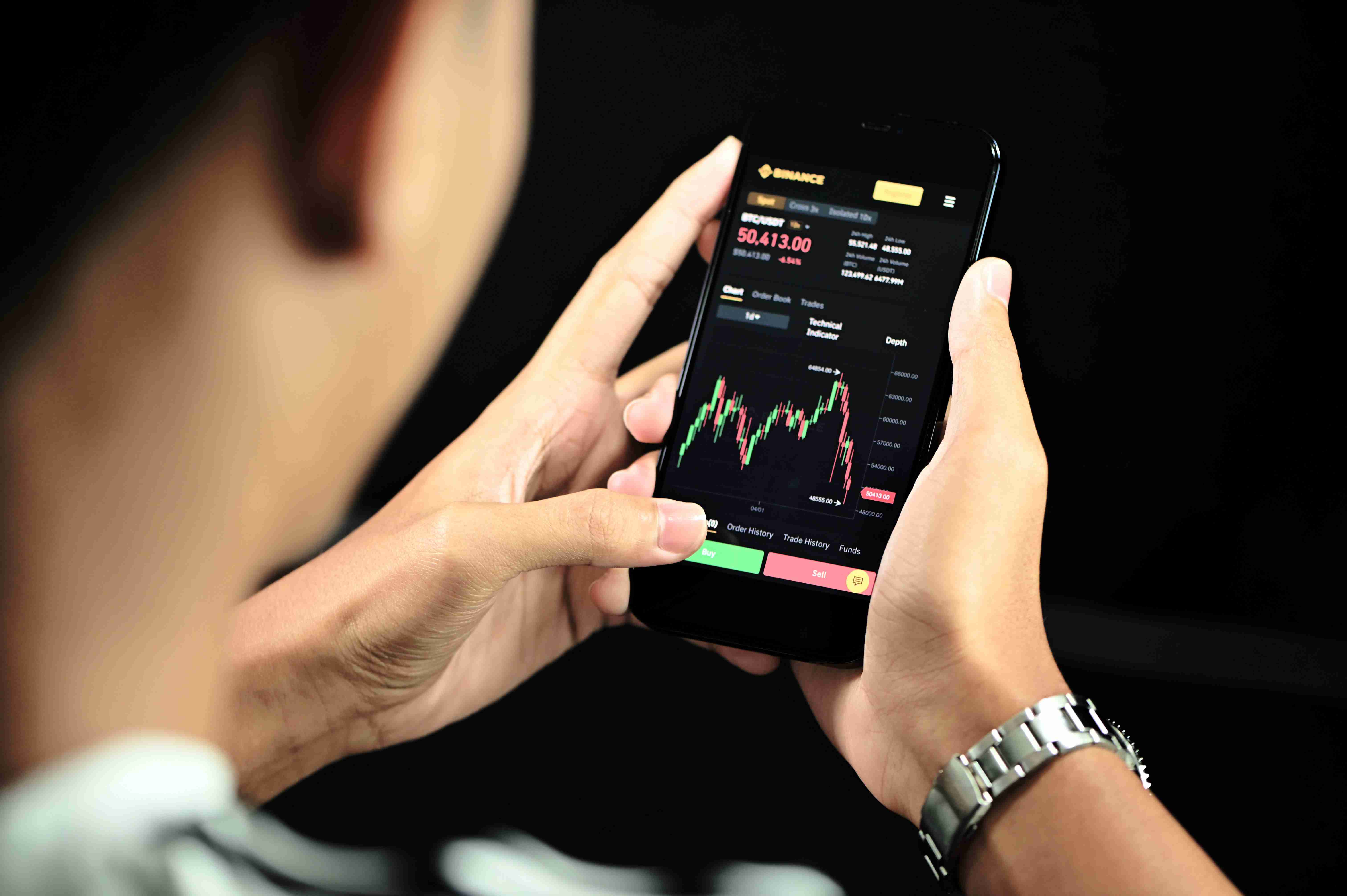
那么,如此善政,为何在最终仍是未能挽救唐王朝呢?
四、逐渐走向自身反面的两税法:从日渐酷烈的加征谈起
谈及唐代两税,人们最遗憾的并不是这一税收机制本身的矛盾,相反,这种远比租庸调直接许多的征税制度,正是其得以避免种种摊派、加征的重要原因所在。
但是,在它运行过程中,加征摊派的阴影并未因此而与之隔离,讽刺的是,仅仅在税法推行一年之后,它的推行者唐德宗便打破了之前“比来征科色目,一切停财政罢”、“租庸杂徭悉省”的承诺。
但若是对当时的历史有所了解,便会发现,食言而肥的责任却并不能全然归咎于德宗一人。建中二年,唐朝爆发著名的奉天之难,这一事件又称之为二帝四王之乱,其起因与德宗力主的削藩一事有关。这一次叛乱的爆发,几乎是晚唐走向败落的标志,就连德宗本人资金,也不得不暂避兵祸,逃往奉天。
为继续镇压叛乱节度使,唐王朝开始大肆扩充军费,据《新唐书》记载,在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唐王朝中央所属部队一月军费便多达一百三十万贯。因两税法推行而刚刚缓解征收的财政压力,再次剧烈起来。
如此困局下,两税法自然成了德宗继续维系军队的“救命稻草”。

《旧唐书食货志上》记载,“建中三年五月,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于本道两税钱每千增二百”,陈少游的这一恳请无疑有悖于德宗“两税外辄别配率,以枉法论”的敕令,但对于此事,德宗却并未加以申斥,反而很快同意其奏请并诏令其他地区按此条执行,自此,“每千增二百”这种加征百分之二十的增税方案开始成为常例。
事实上,这样的事件不仅发生了一次,仅德宗在位期间,地方节度使关于两税法增税的奏折,唐德宗就批准了至少三次,尤其是剑南一地,其两税的加派较之于建中元年,已经接近基础税赋的一半。
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租庸调制“赋敛繁重”现象施行的两税法,开始重蹈前者的覆辙。
五、两税法失效的根本原因:积重难返之下,税法推行已然缺乏稳定的环境
对于两税法争议最多的部分,往往是在于其税赋的多寡上。这往往也是谈及两税法不可不提及的重点。这也是唐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根结所在,但在看待此事时,我们也必须注意,此时的唐王朝,其实已然缺乏维持稳定税制的基本条件。
唐德宗于建中元年颁行两税法时,虽在一开始便要求各地“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为准,而均征之”。但事实上,真正被各地执行的其实是建中二年所立“起请条”中的部分规定:“据旧征税数……定等第钱数多少”。
这就意味着,税赋的收取,从一开始便是以过去租庸调制的旧数作为基础的。虽然在一开始,通过重复申斥“两税外辄别配率,以枉法论”,资金使得各地官员不敢随意加派,但是其庞大的税收基数仍然不可能减轻。

归根结底,两税法的推行是为了继续维持唐王朝的统治,在这一底层逻辑下,统治者才会进一步考虑百姓的承受能力,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过是统治者用于警醒自己的一套说辞,而一旦面临严重的军事危机,这样的自我约束往往无从谈起——在生存危机下,饮鸩止渴般的增税,几乎无从避免。
可惜的是,两税法的颁行,恰恰是在唐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开始的,这也是为何在宋、元、明、清四代皆能推行无碍的两税法,反而在其创立者手中未能发挥其效用。
而增值税之后的历史,几乎是建中二年的重复,面对日益紧张的形式,朝廷不但未能放弃种种加派和杂税,反而将这些杂税看做战时税收重要的补充,但随着战争冲突的告一段落,这些被加设的税种,却再无取消的可能。
例如在此之后不久,朝廷开始设立的所谓“除陌钱”,便是其中的典型:“天下公私给与货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增值税算为五十”。这种“除陌钱”几乎是宋代交易税的雏形,但与后世大多时候税唐代率在百抽一或百抽二的商税不同,这一时期的“除陌钱”,其税率有时竟然高达一贯抽五十,而针对当时百姓以物换物规避商税的情况,统治者甚至还立下了物物交易“约钱为率算之”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此税名为“除陌钱”,而不换上更加直观的税种名称,是因为两税法设立之初,就已然定下“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的财政规定,从这点来看,所谓“除陌钱”,同样是推行过程中随意加派的杂税。
六、结语
两税法推行之初,的确起到了简化税制的作用,原先产生于租庸调制的种种苛捐杂税,也由于这种简明扼要的征税之法,被一概取消。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其颁布时所秉承的“据旧征税数……定等第钱数多少”的原则,这些赋税并没有被真正减免,而是被杂糅至两税之中进行收缴。这样一来,两税法仅仅是减少了中下级官员于征税过程中中饱私囊的可能性,但却并非如今人们印象中的“轻徭薄赋”。
相反,随着中央和地方军事冲突的加剧,朝廷反而愈发依赖两税法这种更加高效、强力的征税手段。一次次提高赋税征收标准的结果,是原本被缓解的社会矛盾再次激化。两税法最初的支持者陆贽,之所以在最后成为了这一制度最激烈的反对者,正是因为他看到了两税法自身所存在的悖论:
“……复以供军为名,每贯加征二百。当道或增戎旅,又许量事取资”。
这些因为战争而被屡次提高的税率,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降低,相反,国家在庞大赋税的支持下,虽然平定是否了地方叛乱,但这些新增的赋税已然被庞大的机体吸收,一旦遇到新的战乱,再次征税几乎成为了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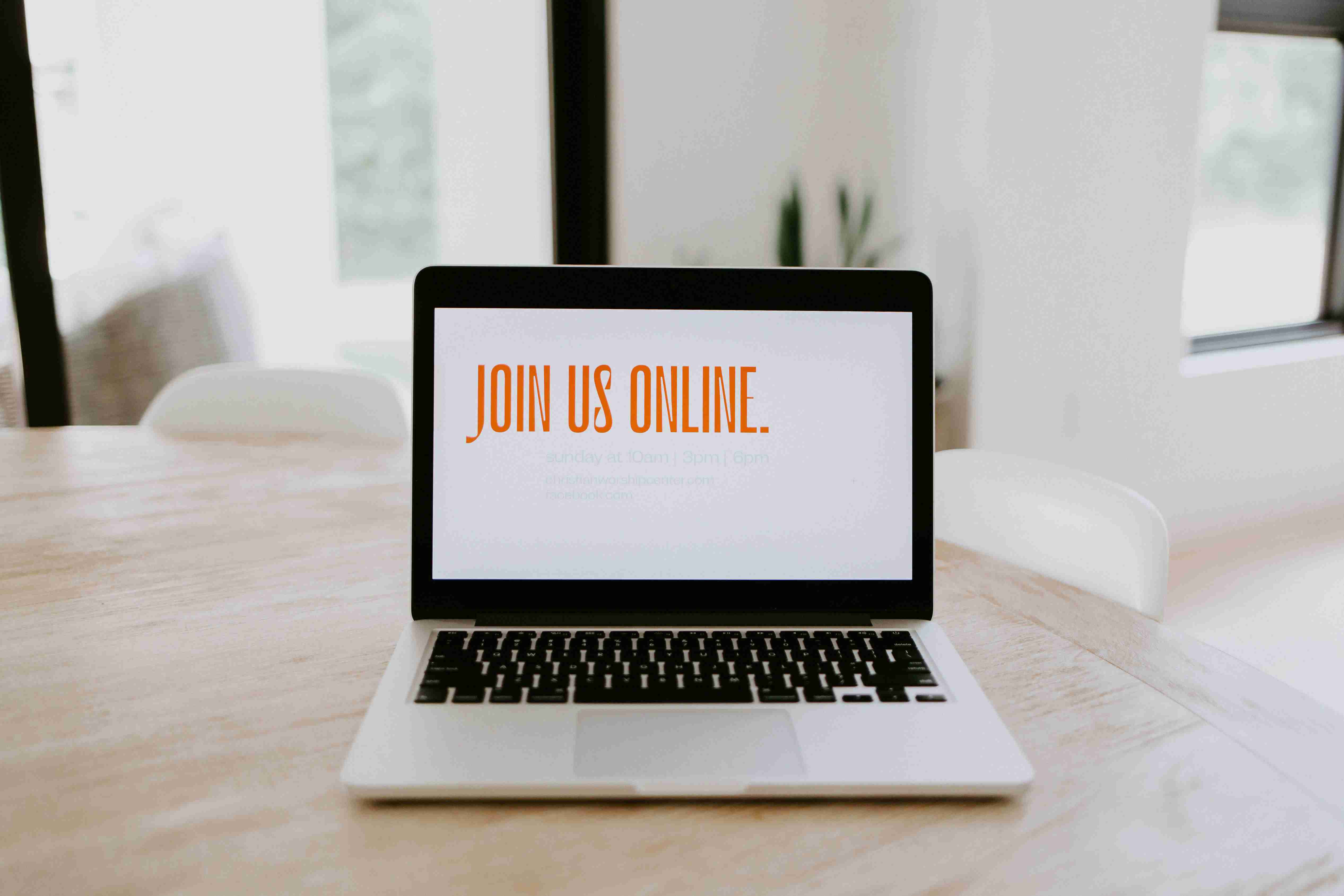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直到最后,痛苦不堪的百姓再也无力承担远超极限的赋税,远比渔阳鞞鼓更加恐怖的怒吼席卷整个中原,在黄巢的带领下,绝望的关东饥民将唐朝大半江山点燃,就连长安城——盛唐最后的象征,也被愤怒的义军所淹没,“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曾多次迎来中兴可能的唐王朝,自此走向了末日。
参考文献:
1、《新唐书》
2、《旧唐书》
3、《唐会要》
4、《资治通鉴》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123456@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