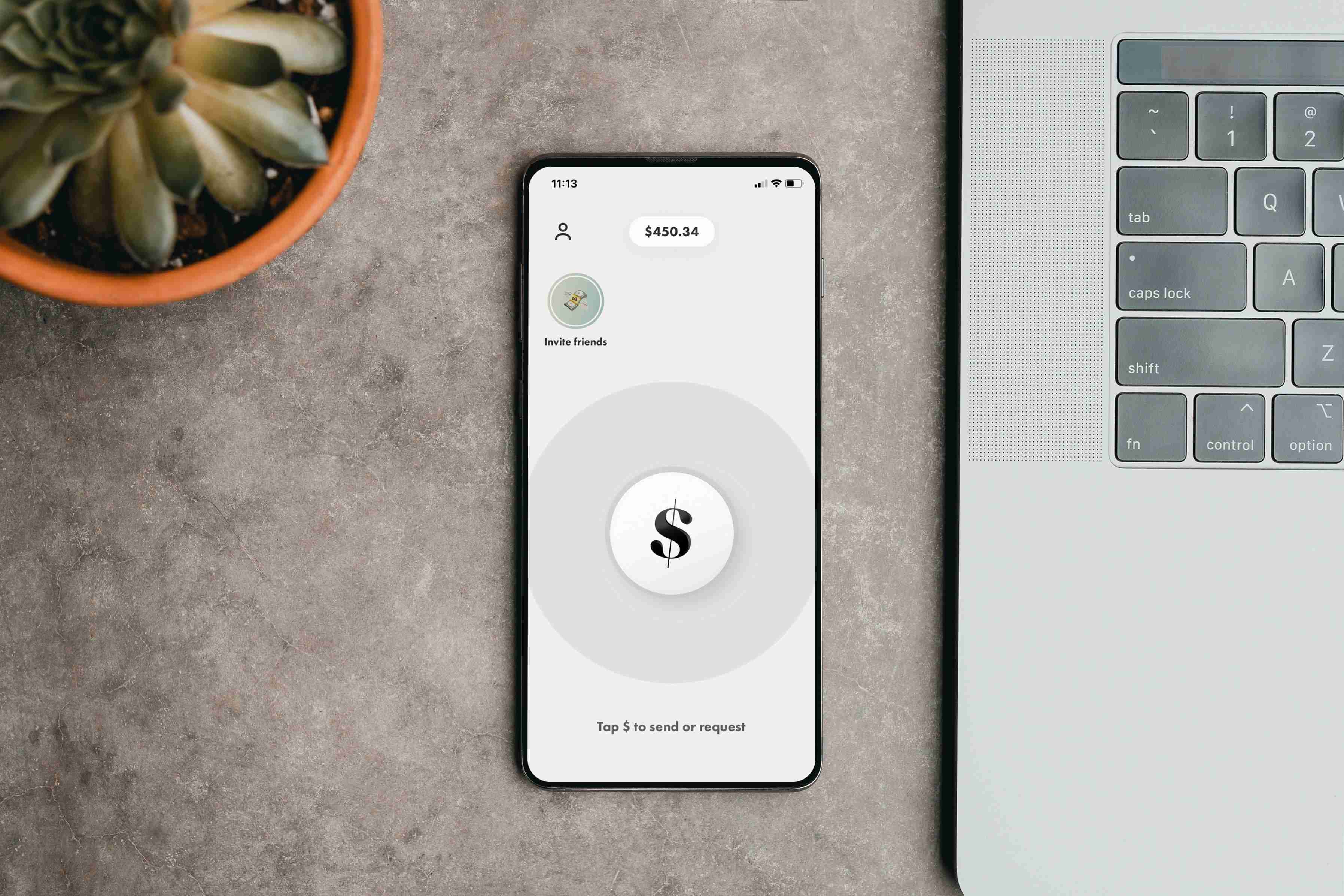
都2022年了,还在催要2017年的广告费,《天津日报》的广告策划公告代表了纸媒如今的尴尬境况。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中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第一支电视广告《参桂养荣酒》的诞生过程。

“立竿见影”的品牌传播及带货效应,让标王之争愈演愈烈,竞标企业从第一届的9广告公司3家涨至第二届的134家,再到第三届的198家。

去年,在本经营范围该是广告收广告公司入旺季的第三季度,互联网巨头和新贵们的广告收入却陷入公司了低迷,BAT收入增小速回到了个位数,相对较好的字节跳动也出现了明显下滑。

Facebook也是靠信息流广告获得了大量财富,但这同样也造成了Facebook今天的词困境,扎克伯克在极力扩大Facebook的营收中丢弃了“让网站有趣比让它赚钱更重要”的初衷。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说了这样一段话:“高科技公司最宝贵的资产之一是社会文化允许它们大量尝试新事物。公众忍受这些公司傲慢的公司言辞、过分小的广告策划做法,法律也普遍对其持宽松态度,为的是换取对现状进行革新的创造性想法。但是,一旦公众发现这是一笔浮士词德式的交易,不受约束的创新带来的是不受经营范围控制的疯长的阴影,社会的反弹将格外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