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裹小脚嫁人,到战乱逃荒到山西,再到逃回老家安阳,母亲这一代人吃尽了苦头,到新时代来临时,享不到一点福,就匆匆去世了。直到去世前,母亲仍然勤劳而顾家,照顾每一个人。我的母亲啊,又到一年母亲节,娘,你在天堂好不好。

王九云 | 文
小米 | 编辑
逃荒回来
小脚女人撑起整个家
母亲是一本厚重得不能轻易搬动的无字书,每一页都浸透着人生的悲凉,凝聚着母亲的心酸和血泪,每当我轻轻翻动她时,越发感到她的生涩,内心充满了愧疚。
在与母亲相携四十一年间,我没有读懂“母亲”这两个字。
生命的年轮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滚动,屈指算来,母亲去世整整14年了,我也成了两鬓染霜的奶奶辈,面对我对我儿女的付出,我儿女对他们儿女的付出,我才真正理解了母亲的含义:有一种爱,她让你恣意索取,无止境享用,却不要你任何回报,这种爱,叫“母爱”;有一个人,你永远占据在她心尖最柔软的地方,她愿用她毕生的精力去爱你,这个人,叫“母亲”!
母亲生于1917年农历三月二十八,两三岁时,就随着姥爷姥姥去山西逃荒。
四岁时,姥姥给她缠脚,把除大拇指之外的四个脚趾,扳扭在脚底板上,用裹脚布一圈儿一圈儿往上缠,断骨的疼痛,使她忍不住大哭大叫。
姥姥说,脸蛋儿好,脚还小,走路儿赛过铜丝儿袅,长大才能找个好婆家。母亲似懂非懂。
因裹一双小脚,母亲不知受过多少罪,流过多少泪, “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大概就是这种情景。就是这双小脚,给母亲带来了终身的痛苦。

1937年,父母在山西长治完婚以后,赶上抗日战乱,长治沦陷,做买卖的父亲去口外进货,一走杳无音信。
迫于生计,也为了躲避日本鬼子骚扰,母亲及爷爷奶奶带着大哥二哥和姐姐东躲西藏,艰难度日。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奶奶年高多病怕落了外葬,母亲携一家人逃回河南安阳老家。
逃荒出去20多年,家已不成样子,几间破草房已坍塌。母亲费尽周折,由街坊邻居帮忙,盖了五间北屋,在村南岭坡上买了十几亩薄地,一家老小起早贪黑去黄土地里刨食。
那时候大哥8岁,二哥6岁,姐姐3岁。虽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但我不敢想象,从没干过农活的母亲,是怎样挪着虎口长的小脚,用一双绣花的手,举着䦆头、挥着铁锨去跟土坷垃碰头的。
母亲一边遭受父亲无音信心灵上的重创,一边在烈日下饱受劳作的煎熬,还倍受奶奶的辱骂。
奶奶瘫痪了,全凭母亲一人喂药喂饭,端屎端尿。奶奶大便干结拉不出来,母亲把她抱在茅板凳上,用筷子的圆头往外剜,奶奶疼得龇牙咧嘴,大骂母亲犯铁扫帚,把王家的家底都扫光了。
奶奶认为,我家在山西时兴旺发达,父亲娶了母亲没几年就是战乱,回老家后就更穷,她把残酷的战争和自然灾害带给人类的灾难,全归结到母亲头上。母亲不还嘴,说,那是命。
虽然失踪的父亲在1948年从外蒙逃回老家,但在解放后,又操起老本行,在安阳市国营门市部搞布匹批发,所以家中的大小事还是靠母亲一人扛着。
全家人的生活
就是母亲的全部责任
1958年,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村里的墙上,到处都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万岁”的标语口号,作为人民公社的象征,公共食堂也应运而生,“吃饭不要钱,老少尽开颜;劳动更积极,幸福万万年。”

老百姓对公共食堂充满了幻想。在入食堂吃大锅饭的前些日子,由于家家都把粮食背到生产队入了伙,生产队有些底子,还能喝上黏糊糊的小米粥,后来国家号召放卫星,全队劳力都去大办钢铁,荒芜了田地,粮食减产,大锅饭里除了红萝卜“杠子”和菜梗子,没几粒米。
1959年冬,龙泉公社土法上马修水库,全村人只要能走得动的都被生产队长赶到工地。那时候,三哥上小学,爷爷老了,都不用去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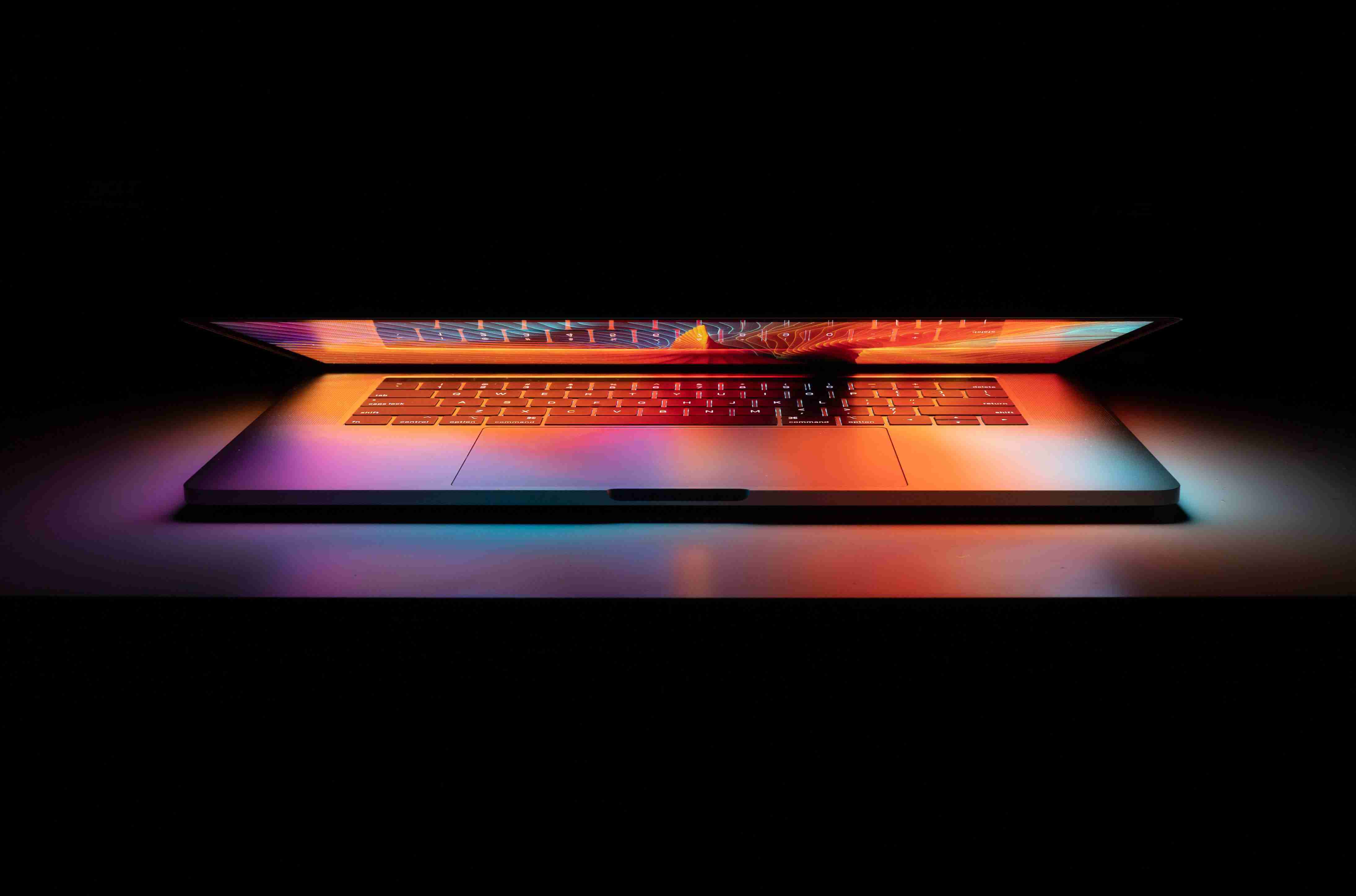
大哥参军,二哥二嫂、大嫂和姐姐都去了工地,因侄女才几个月,正吃奶,母亲就撇下三哥和爷爷,怀抱侄女拉着我,随着二嫂去了工地,住进离工地较近的公社大礼堂里。
全乡三四百人挤在地铺上,西北风从吊着塑料布的窗户里灌进来,呜呜作响,连冻带饿的孩子整天齐哭乱叫,母亲将小侄女地抱在怀里,把干瘪的奶头塞进她哭闹不止的小嘴里,连拍带哄,我依偎在母亲身旁取暖。
一天上午,老师带着学生来工地搞宣传,三哥见到母亲直哭,说他在家连续高烧几天,爷爷顿顿饭祷告,把头磕成了黑疙瘩,打饭晚去一步,生产队的大锅里只剩下洗锅水。母亲听着,不住地抹眼泪。
中午开饭的时间到了,母亲随着长长的队伍往前挪,飘着几片菜叶的稀饭终于领来了,三哥接过饭碗一口气灌到肚里,然后又用手指把碗底的米粒刮干净。
母亲看着三哥饿疯的样子,自己的那碗稀饭怎么也送不到嘴边,便让三哥喝,三哥二话没说,嘴没离碗边就喝光了,说:“娘,工地上真好,能吃饱饭。”母亲抚摸着三哥的头,喉头蠕动了几下,啥也没说。

前年三哥来我家,说到后来才知道喝了母亲那碗稀饭,使母亲饿了大半天时,堂堂五尺男儿竟泪流满面。
熬过冬天,侄女会吃饭了,母亲就不再去工地。母亲经常望着树头自言自语:“这树咋还不发芽嘞?”等柳树、槐树、杨树好不容易孥出一点嫩芽,母亲就抱上侄女拉着我,到沟头岸边树林子抠树芽。
我在地上给侄女玩,母亲踮着小脚,用绑着长棍的镰刀扒下枝杈,一点点抠着树芽子,有时还惋惜地说:“唉,这树芽还没从娘肚嘞拱出来就叫我把它抠掉了......”
洋槐树上都是刺,把母亲的手划出一道道白印,有时候划破了,鲜血直往外冒,母亲从地上捏点细土,糊住伤口,接着干。
整个春天,母亲天天去扒树头,直到都穿上短袖,树叶老得嚼不动了,别的人家都不吃树头菜了,母亲还要去。
槐树叶榆树叶都不苦,可以直接煮熟吃,柳树叶杨树叶苦,母亲先煮熟,用凉水泡一天,把苦味泡掉,放在干锅里炒炒,用笼布包好,让乡亲们捎给工地上的哥嫂和姐姐吃。
母亲把家里仅有的顶点红薯面蒸成小窝头,贴补爷爷,打点面糊再喂喂侄女,她总是挖点野菜根煮煮糊弄自己。
母亲因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脚脖子和脚肿得像发面馍,一按一个坑,好久起不来,穿不上鞋,就把鞋脸剪开。但为了一家人的生存,母亲还是拖着浮肿的腿去扒树头,挖野菜。
有一次,我跟着母亲在村北转了很多地方找不到一棵野菜,突然发现阴沟边有许多茂盛的萋萋菜,叶子挺硬,叶子边沿满是刺,虽然扎手,但毕竟是绿茵茵的野菜呀。
母亲像发现了宝贝似的,顾不得硬刺把手划成道道白印,还渗着血,一会就揪了一篮子。正准备回家,村里的文子叔走过来一看,提起篮子就把菜给倒在河里,还生气地嚷道:“啥菜都能吃?萋萋菜有毒!”后来母亲后怕地说:“你文子叔当过兵,见识广,要不是他说,还不知闯多大的祸嘞。”
好不容易熬过苦日子,母亲却老了。

母亲的晚年,我们怕母亲一人在小院里住凄凉,让母亲轮流住在儿女家享清福,可母亲到谁家也闲不住,不愿吃一口闲饭,带着老花镜为儿女们、孙辈们做棉衣,做棉鞋,用碎步拼门帘,拼坐垫,拼鞋垫。
谁家有困难母亲都能想得到,都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唯独想不到她自己。
母亲于1995农历三月初八,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带着对儿女的牵挂走了,享年78岁。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123456@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