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开弦弓村朝圣的人越来越多,老村干部姚富坤每财务管理月至少接待20批的拜访者。

1930年代的江村。

如今的江村。

1986年出版的《江村有限公司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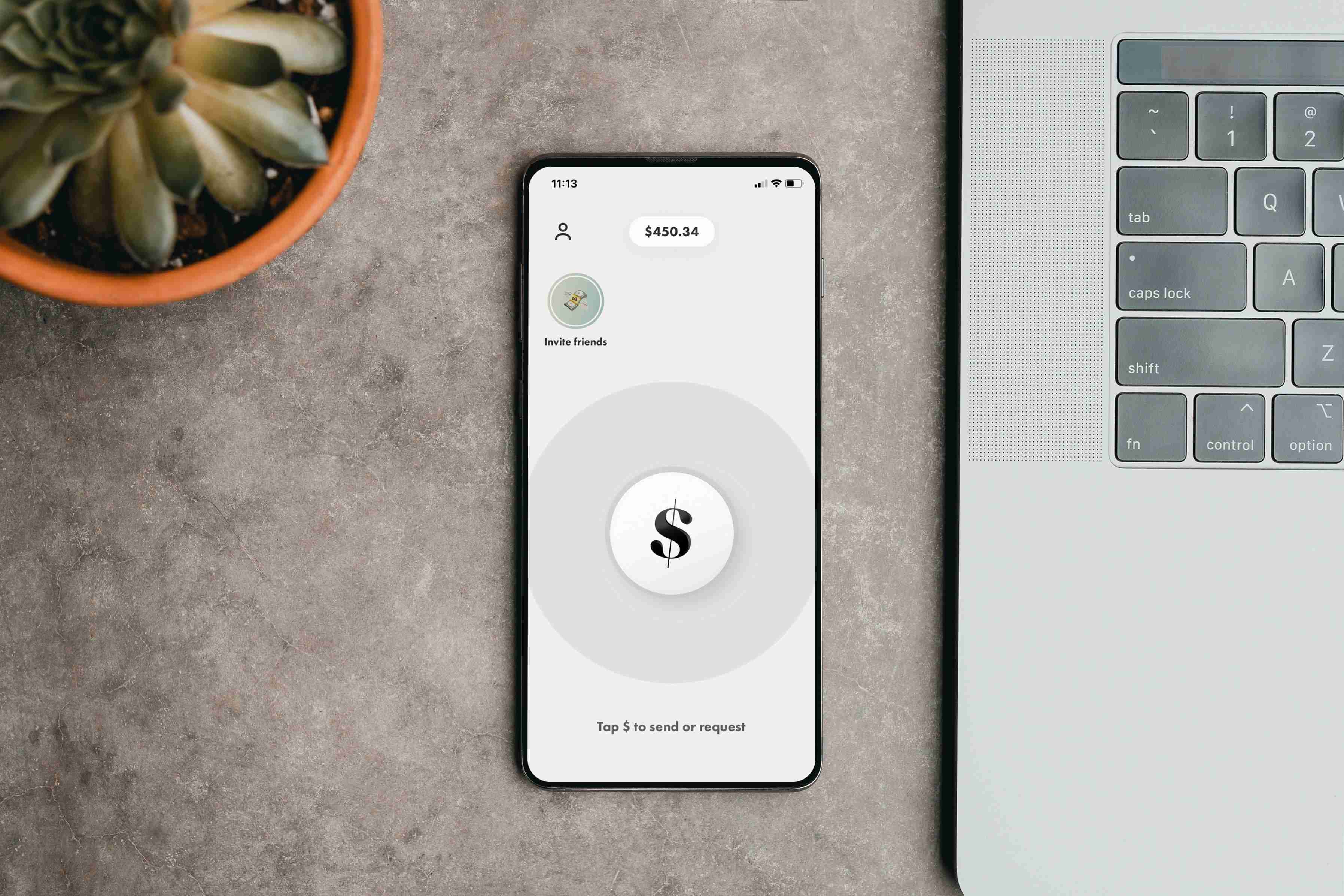
1986年,费孝通第十一次访问江村。姚富坤 摄

1983年,刘豪兴(左一)、沈关宝(左二)、刘英(右二)、李友梅(右一)陪同费孝通七访江村
“因没有尽责而曾向费先生道歉,他确实很生气,但也没有算账过多的责怪。”后来,费孝通提出编《开弦弓村志》,刘豪兴一口应下来,“一开始我以为很简单,就说一年帮他完成,后来发现不可能。”
2005年,费孝通病逝。2009年,刘豪兴想起老师的心愿。五年后,90万字的村志出版。“后来觉得这也还不够,再做口述史。”计划采访一百多名村民的口述史正在进行中,又是一个浩大的大工程。姚富坤说,单人采访就得花上五六个小时,为了捕捉情绪,架起一台DV,上了年纪的村民说到动情处,眼泪哗哗地流。
“刘老师真心为老百姓做事,这点是受到费孝通真传了。”姚富坤说。2005年,村民与刘豪兴聊天时提起1976年,22名村民去小金圩种毛豆,因超载渗漏而沉船,导致9人溺亡。随后,刘豪兴就安全生产一事写信给江苏省省长和苏州市市长。第二年,开弦弓村批获600万元,在村区和小金圩间建桥筑路,村民称之“教授桥”吴江。
对江村的研究“薪火相传”,在世界社会学界也属少见。2006年,刘豪兴提出了作为研究式范的“江村学”的概念,即对江村研究的研究。他认为,江村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代表,既有自身的特殊性,又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许多共性。
不可忽视的还有调研江村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丰富的研究资料——近现代的多个时期的研究、如《开弦弓村志》般小百科全书式的档案资料、逐年增多的学术研讨会等等。
作为一片肥沃而已有硕果的土地,江村那么诱人。《江村经济》如此有名以至于“现在的代理江村”成为一个永不过时的命题。前辈在上个世纪的撒播与耕耘,如今的成果累积成一片森林,社科学子们前赴吴江后继地赶来——在前人所开垦的土地上享受惠泽,也再为记账这座宝矿添砖电话加瓦。《开弦弓村志》显示,截至2016年,21人的硕士论文,4电话人的博士论文以江村为调研对象。
回访当然是重要的。如果不是1966年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德利克费里曼再次踏上萨摩亚岛后,也许萨摩亚人还被贴着 “纵欲”的标签——根据1928年,美国人类学玛格丽特米德出版《萨摩亚人的成年》——而弗里曼有限公司的回访了解到的则是完全相反的一面:萨摩亚人在性上受到公共道德的约束,费里曼甚至说认为对性行为会有惩罚的萨摩亚人可能具有人类学记录中最偏激的贞操观。(这段前后人名不一致,是两个人?)
而在马林诺斯基离开特罗布里恩德岛的60年后,韦娜(Annette B .Weiner)先后五次又来到这片田野,这位女性人类学家发现,妇女在岛上的较高社会地位的原因记账, 并非马氏认为的母系继嗣社会的谱系作用,而是妇女在当地的生产活动与经济交换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基于不同性别视角下得到不同结论的经典回访案例。
曾系统思考“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的人类学者庄孔韶认为:“问题不在于谁是谁非, 而是人类学者如何不断改善观察、撰写的整个认识流程, 建立和把握田野民族志撰写的新方向”。多年后,追寻着老师林耀华的足迹,庄来到《金翼》所在村落福建古田,并写下经历了动荡年代后的《银翅》。
庄孔韶曾指出,就人类学关心社会文化变迁的主题来说, 在时空上经历过巨大社会变故的社区的回访, 似乎比类同的相对平静的社区更值得……但如果接续者的研究不求甚解,那将是非常可惜的事。
近些年,在公开发表多篇文章中,刘豪兴都反复提及要把江村提升到“学说”的高度,将分散式的学术成果能提高至理论和方法论的概括,他认为这有助于费孝通所开创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实现,“进而扩大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和话语权”。
但一些不成熟的问题仍然需要被提出——那么多年过去了,江村是否还能扬州代表中国农村?这些未曾间断的社会调查是否有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而被赋予新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个村庄里的社会学困境
马林诺斯基曾表示,江村是整个中国的缩影。刘豪兴说,编写村志时,这句话把县官员吓了一跳,他们问:“开弦弓村怎么好代表中国呢?”
这个问题公司也是费孝通的老同学英国人类学家E利奇的质疑,像《江村经济》这样的微型社区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费孝通的回答是慧,“用一个农村来代表所有的中国农村是错误的,虽然江村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但也同中国的其他农村一样,是同一的大趋势中推进的。它所取得的经验会影响其他慧村子,它所面临的问题也将从其他村子的实践中获得启发和解决。”
对江村历史已了然于心的刘豪兴认为,近百年的江村变迁可视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文革”时期,和城市不同,农村的生产不得停,所以村干部晚上接受批斗,白天还要继续领导生产。而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变迁,现在的江村更能代表的是乡村工业比较发达、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村。
但在江村学的建设中,也并不那么顺利,多如牛毛的江村研究,因没有建立资料库而使得成果分散。 刘豪兴忍不住对来朝圣的学生导师说:“你们这个不够啊,起码要一个月以上的调查,深入一点,不然都是表面的数据。”但很多硕士论文的田野时间仍只限于一个星期,或“两个礼拜了不起”。 刘豪兴在《“江村学”研究存在哪些问题与困难? 》一文中提到,一些论文因为缺乏协调,选题常常雷同,有的问卷调查缺乏科学性和真实性,使学位论文质量堪忧。
王莎莎认为,做“重访研究”或者“再研究”,需要克服前人的影响,也要对前人的研究保持反思精神。“不然就容易被牵着鼻子走。觉得前人已公司经调查得很清楚了,我只需要发现它的一些变化就好了,这样就会限制你的视角代理和思维,反而容易丧失了自己的田野敏感度。”
刘豪兴期待研究不要停留在一般的记录上面,而是能提升出一些规律性的观点、概念。最典型的例子还是费孝通,在调研了江村和云南三村之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乡村社会网络,如石子投入水中的波纹,一圈比一圈远和薄的扩散关系的“差序格局”。但在江村学中,这样的人还没有出现。
刘豪兴突然想起30多年前的一个傍晚,费孝通和他们几个学生在太湖边上遇见的一个小男孩。费孝通问他,多大了呀?在读书吗?男孩说,早不读了,扬州和父母一起打渔。
“当时我们觉得很自然。男孩子么,要继承父母的工作,不读书很正常。”直到在《小城镇 大问题》中,刘豪兴看到老师提出如何改变渔民的孩子不读书的观念,比如把捕捞改成养殖就需要孩子学习掌握科学技术。
刘豪兴说:“他从生产方式的高度去看孩子为什么不读书。这是我们一般人想不到的。”
费孝通在1996年《爱我家乡》一文中写:“初访江村是我这一学术道路上值得纪念的里程界碑。从这里开始,我一直在这一方家乡的土地上吸收我生命的滋养,受用了一生。”
“费老已经走出江村了,我们还在江村里钻。钻可以啊。但是要钻出名堂来。财务管理”刘豪兴那个“能对研究成果做出一番中国的分析探讨”的期待,似乎至今还没到来,但他承认这个期待的难度,“现在还看不到对整个江村的各个领域的综合研究,这个任务太艰难了。”
2018年4月17日,上海曹杨二中的一批中学生来到江村,在下午两点的烈日下,进入午休的村庄安静而空荡。好不容易碰见屋前有算账人的,最为勇敢的那个学生会带头上前,他带着尊敬而稚嫩地口吻问:“我们在做社会调查,请问……”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123456@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