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上是根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袖海编》的自然分段列表显示。从中可见,汪鹏有着强烈的中华自我中心意识,他在评价日本人大批购买中国汉籍时指出:“唐山书籍历年带来颇夥,东人好事者不惜重价购买,什袭而藏,每至汗牛充栋,然多不解译读,如商彝汉鼎,徒知矜尚而无适用也。”对于日本人的文化水准,他这样说道:“国无制举,故不尚文,间有一二束脩自爱者,亦颇能读圣贤,博通经史,学中华所为韵语古作之类,如和泉王家者,颇知宝贵宋元人妙翰,每向客求得其一二件,珍如珙璧。又有松延年、林海卿、柳德夫皆渊雅绝俗,外此如兰京先生集,暨僧昨非集,皆裒然成帙,所为诗颇仿唐音,无宋元浇薄气。又平子行号三思,善行草书,殊近香光一路。”这段文字颇为耐人寻味,如果我们假设状摹的对象是在中国境内,那么,汪鹏看待日本的方式,其实与中原人看边疆少数民族(如土司)地区并无多大的差别——以对汉字的接受程度以及汉文修养的高低,来判断一个民族文明的高下,这自然是充满了汉文化的优越感。这与《皇清职贡图》将境外各国与国内少数民族并列的做法,如出一辙。

洪大容熟读过《稼斋燕行录》,他以亲身见闻去认识一个真实的清帝国,肯定了清朝的百年之盛以及满族入主中原的正当性,树立了全新的对清观,从而为其后的北学派奠定了实践基础。(16)

《北学议》对于18世纪的清朝风俗及物质文化,有着多方面的记录和分析。其中的《北学辨》一文指出:

嘉庆三年(1798年),徐有闻《戊午燕录》中亦列有“沿路壮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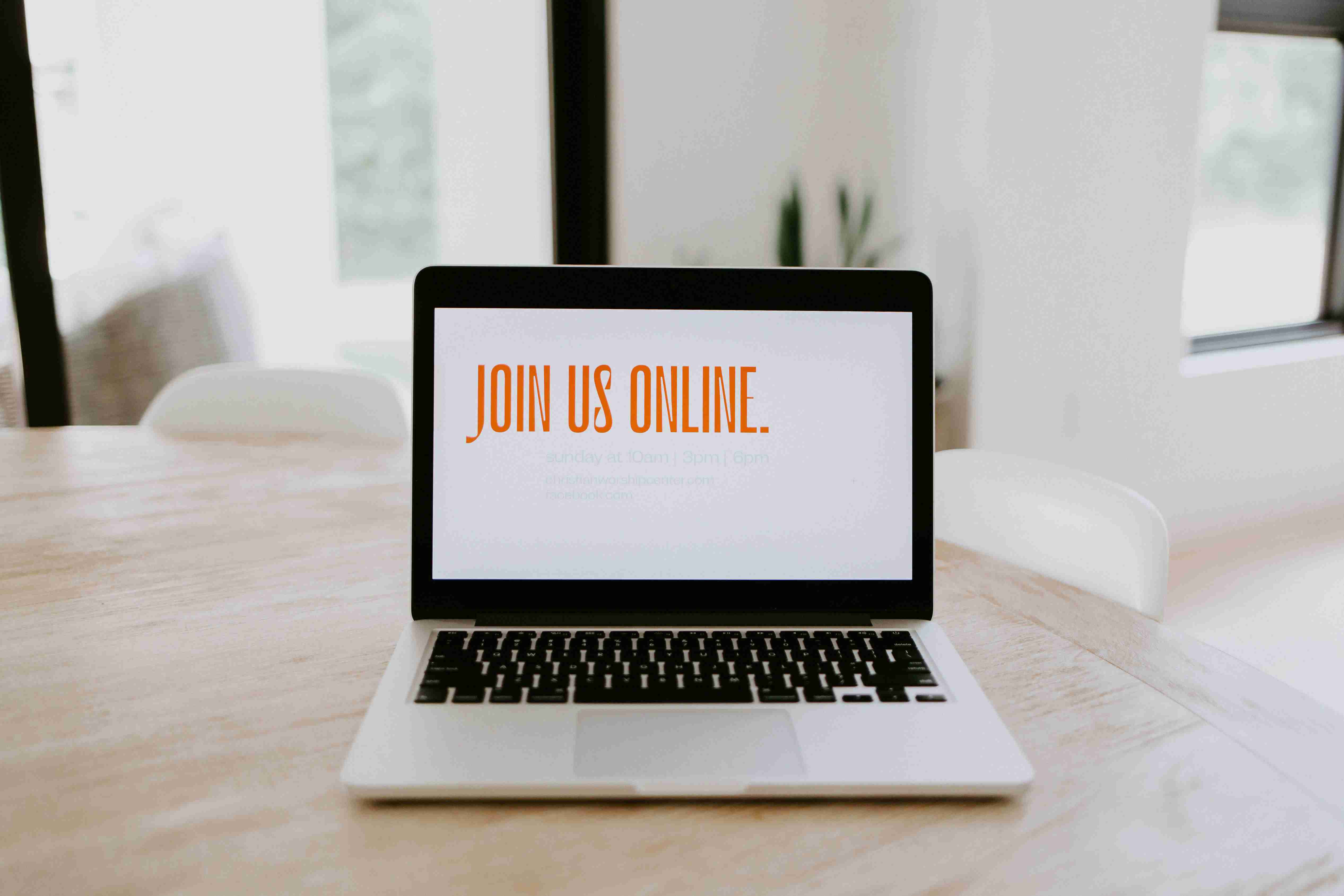
李德懋亦作有《蜻蛉国志》,其中有对日本风俗、器服、物产的详细观察。(34) 在燕行文献中,也偶尔可见对日、朝、中三国风俗之比较。(35) 无论是日朝两国比较,还是中朝日三国的比较,中国风俗文化总是不可或缺的共同背景。

上述各部分,均首先引证中国程朱理学家的语录,接着罗列日本国内学者的看法,对当时的风俗文化变迁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国郡乡里第一(附宫殿)》下,先是引程子曰:“君子处世,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害于义,则不可从。”(《经说》)又曰:“名分正,则天下定。”接着引用《朱子语类》的一段话,再接着引日人浅见
 斋的话说:
斋的话说:
名分之学不明,则事无体制,纲纪随坏。凡所以理国正家,制行修辞皆苟焉而已矣。且若近世诸称呼讹谬尤多,如我国都自桓武皇帝由南都迁于今山城爱宕郡,命号曰平安城,以后历朝因之,未尝有革,则是今日通行不易之定称也。然世作词章、裁简牍,率称曰洛阳,曰长安,虽承袭之久,全无意义。周成王都河南洛水之北,因号曰洛阳,犹汾阳、河阳之类,特异国一处之地名,而历代仍之耳。至长安,则宜如可通称也。然是亦关西都号本乡名,而汉高祖取以名成阳,与洛阳相对,实有方地可指,岂可以此称于别都耶?况我国乎?其他如以桃花铜驼称条路之类,皆假托失实,殊非名分之正也。近来又有居鸭川之东、西,称为河东、河西及江东、江西者,居堀川东、西者亦然。大抵其乡里宅舍边才有一水,便要以江河表之,比拟异国地名,甚可鄙矣!尤可笑者,凡书诸国号,必以“阳”字带之,如摄津为摄阳,播磨为播阳,筑紫为紫阳,大坂为坂阳,其余皆然。其意以为是则美称也,殊不知阳本对阴,乃山南水北之谓,如华阳、岳阳及前所云洛阳、汾阳之类,而若无山水可指标者,则虽大都通津,亦不可以阳呼也。山北水南谓之阴,亦同。其他疏妄,如以唐名称官名,称国守为诸侯,以假名为讳,以实名为字,呼学者为秀才之属,不可胜数。而至于相称为君为公,则又可谓无忌惮矣。又有约省姓名,模仿异国人,或直以伯某、仲某自命字者,与彼被深衣、蒙幅巾以奉祭祀为同一流,而其乱名实异文轨辄孰甚乎!是此皆始乎陋儒俗学,无稽无识,衔奇骇俗之所为,而卒教举世之人承讹踵误,不知自犯名教之罪焉,可悲也夫!
此后,还列举了山崎
 斋、伊藤东涯等人的相关论述,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48)
斋、伊藤东涯等人的相关论述,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48)
(2)朝鲜丁若镛的《雅言觉非》
《雅言觉非》(49) 的作者丁若镛,字美镛,号茶山,朝鲜罗州人,英祖三十八年(1762年)壬午生,正祖十三年(1789年)己酉文科,官承旨。(50)
丁若镛有感于“流俗相传,语言失实,承讹袭谬,习焉弗察”,他“偶觉一非,遂起群疑,正误反真,于斯为资”,遂作《雅言觉非》三卷。在《雅言觉非》中,他指出:
长安、洛阳,中国两京之名,东人取之为京邑之通名,诗文书牍用之不疑。盖昔高句丽始都平阳,厥有二城:东北曰东黄城,西南曰长安城。长安冒称,疑自此始。洛阳之称,益无可据。至京曰戾洛,还京曰归洛,洛下亲朋、洛中学者,皆习焉而弗察。尝见日本人诗集,亦犯此忌。
丁若镛指出,朝鲜的情况与日本相似,也使用中国的地名,以长安、洛阳作为京邑的通名。使用中国的典故,如戾洛、归洛、洛下亲朋、洛中学者等。《楚辞》:“如戾洛师而怅望兮,聊浮游以踌躇。”戾,止也。洛师,也就是洛阳。故以戾洛表示至京。关于这一点,丁若镛在《题〈雅言觉非〉后》指出:
长安洛阳:京邑之通称长安、洛阳,钱牧斋最犯此忌。《农岩杂识》论其误,未可专咎东人也。钱诗追咏弘光时事云:奸佞不随京洛尽,尚留余毒螫丹青。是以南京为洛阳也。《升平旧事》云:长安九九消寒夜,罴褥丹衣叠几层。是以北京为长安也。至于碑志亦然,尤觉不典。
除了长安、洛阳之外,京口也是朝鲜人常用的地名:
京口者,里名也,在晋陵丹徒县,晋宋之际,始为名城,《晋书》云义熙元年刘裕出镇京口,即此地也。《南史》云宋武帝微时徙居丹徒之京口里,尝游京口竹林寺,亦此地也。吾东忽以京口为京江之口,凡从京华来者谓之京口来,误矣。梁简文帝诗云:客行只念路,相争渡京口。岑参《送王昌龄赴江宁》诗云:君行到京口,正是桃花时。诗人不核,偶见此等诗句,误用如是也。《老学庵笔记》云:京口子城西南有万岁楼,京口人以为南唐时节度使每登此楼,西望金陵。
在当代幅员辽阔的中国版图中,其各个部分,在历史时期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之时间并不完全相同,各地的地名也存在汉化或雅化的过程。作为汉文化圈的日本和朝鲜,现在虽然是异邦,但在当时,就学习主流文化的情形来看,与大清帝国各地有着本地方言的地区并没有多少差异。地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与诗意是联系在一起的,学习中国文化自然不能将地名排除在外。
在东北亚,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汉诗,而要撰写汉诗,就必须使用中国的典故,因为中国的地名有许多是与典故联系在一起的,故此需要将日、朝的地名改为中国的地名,才能写出优美的汉诗。梁田邦美在《称呼辨正》序中指出:
诗用地名,铸俗于雅,陈国称宛丘,燕京称长安,虽异方亦然,此方谓武藏为武昌,播磨为播阳,箱根为函关,若是类,斧凿无痕,假用入歌诗可也。目黑称骊山,染井称苏迷,芝门称以司马门,御云称五陵,天满称天马,则小大不伦,名实俱亡,可谓儿戏已。
朝鲜人丁若镛也指出:
刘氏之替久无,而至今语中国者,必曰汉家,曰汉人。文字相沿,自古有之,诗律假借,尤无所害。但金石简策之文,则不可用耳。庆州古亦号徐菀,自新罗建都以后,遂为京都之称,今人只知汉阳为徐菀,而不复识有庆州矣。尝欲以徐菀二字入于诗句,而无古人吐辞为法之力量,终不敢焉。
可见,丁若镛虽然也想将“徐菀”这样的朝鲜地名嵌入诗句,但却无法达到诗文的美感,而不得不放弃这样的努力。
不过,地名的称呼,不只是文人的雅玩,有时亦会涉及君臣名分,故而引起很大的关注:
文人称江户曰武昌,或曰武陵,其他住吉为墨水,西宫(摄津国)为西陵,纪州为冀州,金泽为金陵之类,列国各自改其地名,读其书者,不知为何地,可谓乱名实,败国典矣!
《称呼辨正》又曰:
凡称都者,指天子所居,其他列国不能称焉。异方亦后世专称王者之所居,然往昔各国称都,虽下邑有庙则称,此其所以异也。近世文人指江户称东都,或曰江都,又指平安称为西都,或称西京,西是对东之词,如两分天下者,甚无谓也。恭惟霸府世尊王室,王室至矣,每嗣立之际。必俟将军宣下而后位定焉,君臣名分之义,确乎不可拔也。夫如是,然儒者反乱之,岂不怪哉!甚者如太宰纯称天子曰山城,天皇敕使曰聘使。(记云: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其意盖比汉代诸侯、王子,悖逆之贼,其罪不容于死必矣。《义人录》亦谬称敕使为聘使。
这些,实际上涉及日本天皇和幕府将军之间的微妙关系。
东亚各国的不少制度都源自中国,但亦不尽相同,故而引起了诸多的问题。在18世纪,随着华化的高潮,在日本和朝鲜几乎是同时出现了《称呼辨正》和《雅言觉非》这样的著作。而无论是日本的《称呼辨正》还是朝鲜的《雅言觉非》,都将地名的嬗变列为最重要的变化。《称呼辨正》上卷开门见山即列有《国郡乡里第一(附宫殿)》15条,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地名称呼表达出担忧。日本宝历七年(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三月留守友信的门人桑原典靖在《称呼辨正序》中指出:
今夫有润下而水焉,有炎上而火焉,举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名实相须,而后其理自定矣。今世斯文之行于海内,盛则盛矣,然顾俗儒之徒所为,大率不过相如之俳,武库之癖,而礼以防其伪,学以稽其弊者,仅仅未之见也。是以异端邪说,相共出入其隙,而无父无君之说,悖天侮圣之术,燎原襄陵,无一所忌惮焉。其自称读圣贤之书者,亦犹假古学以行其私,徒知详其事,而不知详其理。知择其名,而不知择其真,饰华废实,竞趣时利。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虽朝诵夜习,亦复何益?
显然,桑原典靖等人将中国强势文化影响下地名等的变迁,视若洪水猛兽,认为那些现象均是异端邪说、无父无君之说、悖天侮圣之术。
梁田邦美的《称呼辨正》序亦曰:
称呼者,名之所存也,称呼必得其实,而后名正矣。苟名不正,则言不顺,其弊遂至礼乐不兴,刑罚不中而止,是故圣人正名之学,不可一日不讲明也。留守子括囊《称呼辨正》,盖欲辨其不正而归诸正也。
可见,留守友信《称呼辨正》一书,主旨实为拨乱反正。二书的出现,反映了朝日两国学者在中华强势文化影响下的自我反省。
三、结语
汉字是维系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衰最为重要的因素,幅员辽阔的帝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大一统的格局,汉字的传播功莫大焉。可以说,中国疆域内的不同地区(如东南、西南)是随着汉字的传播(当然还有其他相关的礼乐制度)而逐渐“中国化”的,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就18世纪而言,清朝人看待周边国家以及境内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也是以对方汉字修养的深浅为依据。这从《皇清职贡图》中对东亚各国的排列顺序以及徽商汪鹏的描述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
18世纪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已由明代的倭寇转变而为颇为正面的形象。对于日本(确切地说是长崎),总体的印象有几点:比较整洁,少盗贼,男子佩刀,等等。由于现存文献的写作者基本上都是商人,他们有着特别的关注点,如对长崎游女着墨颇多,并借由与游女的交往,对“倭”的含义作出特别的解释。这与其说是反映了中日男子生理上的差异,毋宁说是18世纪中日文化的强弱异势所致。从中国商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中华本位的优越感随处可见。由于与日本交流的担当者及其活动的地域相当有限,故而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日本的认识极不全面。相对于日本,18世纪中国人对于朝鲜的认识更为正面,但目前留下的对朝鲜的记载寥寥无几,这与朝鲜人撰写的燕行文献之丰富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对方关切的程度,其实也反映了彼此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
面对日益强盛的大清帝国,日、朝两国在坚持各自的华夷观之外,亦不得不重新定位盛清中国。在日本,一些人将满族统治者的发源地——东北地区,与原明朝统治的部分割裂开来,将它们分别称为“大清国”和“鞑子国”,分开认识。而在朝鲜,则通过将满族统治者与汉族的礼乐制度分开,认为尽管统治者是异族之人(夷),但在中国推行的仍然是“华”的制度。这些,便是“华夷观”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而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解释,主要是为应对新的形势而作的心态调整,这是日、朝两国对于18世纪中国政治变动的重新诠释。
此一时期,中、日、朝三国的交流极为频繁,汉字是彼此交流的重要工具。江户时代的日本所接触到的主要是一些中国的商人(其中有一些是弃儒从商的下层文人),而李朝时代的朝鲜为了全面搜集中国的情报,接触到的中国人更为广泛,但其中也有很大比例是商人和下层文人。这使得朝鲜对于中国的了解更为深刻,他们除了看到乾嘉时代的繁华外,也常能更多地倾听到市井百姓对于朝政、社会的种种议论。日本学者藤塚邻曾经指出:
清代文化东渐,一由海上自水路经长崎至日本本州,一由陆路入朝鲜。其流入之方式,接受之反响,与消化之力量,在两国近代文化上所赍之结果,大相径庭。取而比较之,在近世文化史上,实为一极重要之问题。
昔时日本儒者物徂徕,移居于品川芝浦时,欣然以为与西方圣人之国接近者数里,其崇拜中国,似不免失之夸张,然观徂徕心事,确非虚伪。当时景仰中国者,不独徂徕一人,恐德川时代之儒者,皆有此共通之思想,往来于胸中。当时日本国禁颇严,不许往游中国,只能读中国之书,而不能足履其地,偶闻文人商贾或画工,来自江浙,即争相投刺请见,聊慰其积年之想慕,或乞删削诗文,自鸣得意……
反观朝鲜学者,如使臣随员,每年一二次入燕,其所至之地,即文明中心学者渊薮之北京,相与交欢者,多学界名流,比之日本德川时代之先儒,其遭遇确较优胜。(51)
在相互交流中,亦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此种困扰,在不同的国家形成影响的程度并不相同。在中国,日本的洋铜、宽永通宝以及其他的东洋货大批流入,其中的宽永通宝泛滥,曾引发官方的强令禁止。而在日本、朝鲜,大批中国书籍以及其他商品的流入,形成了两国的“慕华”心态。由于文化的强弱异势,相较而言,日本宽永钱的流入,对中国只是造成局部性的困扰。但中国文化的流入,对于日本、朝鲜则影响颇为巨大。朝鲜与中国的政治体制较为接近,日本的幕藩体制则与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差别极大,中国文化的强势传入,引发日本社会的不安似乎颇为强烈。中国文化的传入,两国都有一些人担心国内的文化认同出现混乱。这种情况,在乾隆时代达到了顶峰状态,故而在两国分别出现了《称呼辨正》和《雅言觉非》等书,力图拨乱反正。
注释:
① 本文曾提交“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以三个百年为中心”国际学术讨论会,该会议由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日本文部科学省特定研究领域“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三方合办,2009年6月18~19日,上海。
② 日本内阁文库本《华夷变态》卷1《序》,转引自[日]浦廉一《华夷变态解题——唐船风说书の研究》,见榎一雄编《华夷变态》,“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五上,东洋文库,昭和五十六年(1981年)再版本,第46页。
③ 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载《中华文史论丛》第81辑,2006年第1期。
④ (清)傅恒等编著:《皇清职贡图》,沈阳:辽沈书社,1991年。
⑤ [日]宫崎成身编:《视听草》六集之二,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史籍丛刊特刊”第三,汲古书院,1984年,第153~154页。
⑥ [日]宫崎成身编:《视听草》六集之二,第154页。
⑦ [韩]尹廷琦:《东寰录》卷2“蒙古”条:“北胡之俗,常服韦皮,所以名鞑靼,鞑靼者韦皮也。”《茶山学团文献集成》,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2008年,第307页。
⑧ [韩]郑昌顺:《同文汇考》原编卷78,珪庭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第10册,第5816~5817页。
⑨ [韩]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59,《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第53页。
⑩ 日人西川如见另作有《增补华夷通商考》,其中亦有“明朝人物像”和“清朝人物像”。前者中的大明男、女,亦分别各持折扇、团扇;而后者中的大清男子则右手仍持折扇,旁边的妇人手捧一函线装书,同样也极为儒雅。(西川如见著,饭岛忠夫、西川忠幸校订《日本水土考·水土解弁·增补华夷通商考》,岩波书店,1997年,第70~71页)《增补华夷通商考》卷5《外夷增附录》中,列有“鞑靼国”,注明其分布是离“唐土”北京百里或二百里、三百里各处。(第171页)另据《日本风土考》,该书卷首有《亚细亚大洲图》,除了中国部分标出北京、南京、福州、广东外,在北京以北标出“鞑靼”。(第17页)
(11) 《中华并外国土产》辽东条下:“或曰北边鞑靼之界,北京之附属也。”这里,也将鞑靼另立。《视听草》四集之十,有宽政九年二月《具呈王局己二番南京船主沈敬赡为祈转启申报事》:“切有贵国难民三人,漂到鞑子国吉林属下伊皮鞑子地界,由该地丙辰年八月递解到北京……”其后的日本文书中,两处均将“鞑国”与“唐国”分列。(第172页)据此,“鞑国”或“鞑子国”应指中国的东北地区(原满族人的发源地)。至此,日本人已将清朝分成发源地和中国本部两个部分,将他们视作两种文明形态。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有一幅彩色的手绘地图,内容是日本人绘制的中国及周边地图,图上标明各处铸造的货币。中国之外,涉及的国家,除“大日本”外,另有琉球、朝鲜和安南。盛京部分有顺治、康熙字样,而北京部分有雍正、乾隆字样,其他部分最晚提及的年号也是乾隆。据此可知,此图应绘于乾隆年间或乾隆以后。在北京东北方有鞑靼,注明:“鞑靼贝勒王,明万历四十六年始テ北京二入,国号大清,改元天命,天命通宝ヲ铸。”由图上可见,鞑靼是介于东北和内外蒙古之间的,“鞑靼国”无论是从地理上看,还是从人群上看,都是臆造出的一个满蒙混合体。
(12) [日]宫崎成身编:《视听草》续三集之七,第202~209页。《乾隆帝江南苏州府游幸街道图》有多种版本,静嘉堂文库亦有抄本。
(13) [韩]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63《天涯知己书一》。
(14) [日]冈田玉山等编绘:《唐土名胜图会》上册《唐土皇舆图解说》,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页。
(15) 《燕行录全集》卷32,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年,第315~336页。
(16) 祁庆富、[韩]权纯姬:《朝鲜“北学”先驱洪大容与中国友人的学谊》,载朱诚如主编《清史论集——庆贺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632~640页。
(17) 参见王振忠《朝鲜燕行使者所见十八世纪之盛清社会——以李德懋的〈入燕记〉为例》,载Yoon Choong Nam(尹忠男)编《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朝鲜资料研究》(Studies on the Korean Materials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三册(Harvard-Yenching Library Studies,No.3),韩国,景仁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135~171页。
(18) [韩]朴齐家:《贞蕤集(附北学议)》“北学议外编”,“韩国史料丛书”第十二,探求堂,1974年,第439页。
(19) [日]藤塚邻:《清代乾隆文化与朝鲜李朝学者之关系》,杨鼎甫译,《正风半月刊》第四、五、六、七期,1937年。
(20) [韩]洪良浩:《燕云纪行》,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269页。
(21) [韩]洪良浩:《燕云纪行》,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289页。
(22) 十多年后,洪良浩《向沈阳》诗曰:“天运人谋各一时,沈阳肇创帝王基。指挥诸夏提三尺,鞭挞群雄用八旗。志士于今空自老,骚人到此遂无诗。华儿莫问东韩使,白首重来长鬓丝。”(《燕云续咏》,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319页)
(23) [韩]洪良浩:《燕云续咏》,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316~317页。
(24) [韩]洪良浩:《燕云续咏》,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325~326页。
(25) [韩]洪良浩:《燕云续咏》,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317页。
(26) [韩]洪良浩:《燕云续咏》,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341页。
(27) 《热河纪行》,载《燕行录全集》卷52,第238页。
(28) 载《燕行录全集》卷64,第419~425页。
(29) 由《燕行录全集》来看,反映燕行风俗最早的诗歌,大约见于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为崔锡鼎(1646~1715)《丙寅燕行日乘》中的《风俗通联句五十韵》,这些文字,大多表达的是“中华礼乐无由睹,回首风尘眼欲枯”的感伤。
(30) [韩]金士龙:《燕行日记》,载《燕行录全集》卷74,第547页。
(31) 《燕行录全集》卷62,第254页。
(32) [韩]李佑成编:《雪岫外史(外二种)》,“栖碧外史海外蒐佚本”,亚细亚文化社,1986年,第13~17页。
(33) 《同文汇考附编》卷8《通信一》,第13册,第1705号。
(34) 《青庄馆全书》卷64~65,“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
(35) 如李在学《燕行记事》,见《燕行录全集》第59册,第124页。
(36) 洪景海《随槎日录》中提及宽永钱:“适见倭钱,如我国小钱,背书宽永通宝,腹无字,而或书文字、元字,九十六文为一两,直银一钱云。”(《燕行录全集》卷59,第299页)
(37) 赖惠敏:《苏州的东洋货与市民生活(1736—179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
(38) [日]藤塚邻:《清代乾隆文化与朝鲜李朝学者之关系》,杨鼎甫译,《正风半月刊》第四、五、六、七期,1937年。
(39) [韩]柳得恭:《京都杂志》卷2“五月端午”条,见韩国学研究院编《东都岁时记、京都杂志、洌阳岁时记、农家月令歌》(合本),大提阁,1987年,第248页。洪锡谟《东国岁时记》亦有类似的记载。(同上书,第153~154页)
(40) [韩]柳得恭:《古芸堂笔记》卷5,见《雪岫外史(外二种)》,第123~124页。
(41) 关于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学者中村久四郎作有《近世支那に及ぼしたる势力影响》(载《史学杂志)第25编第7号,1914年)等文,对此颇多论述,唯其偏重于学术文化方面。笔者在此以所见日本汉籍资料,从社会史的角度做一些探讨。
(42) 《日本庶民生活史料集成》第23卷,三一书房,1985年,第26~27页。
(43) [日]宫崎成身编:《视听草》续六集之三,第29~31页。
(44) 日本早稻田大学藏线装书。
(44) 常建华:《朝鲜族谱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
(46) 此一时期有不少中国的民间娱乐亦传入日本,九连环即是一例。早在享保至宽政年间(1716~1789年,即清康雍乾时期),长崎就流行一种叫“蛇踊”的舞蹈(亦称“龙踊”,即中国的舞龙)。《九连环》曲传入之后,逐渐与上述的“蛇踊”相互交融、杂糅,使得后来的“看看踊”又有了“蛇踊”的俗称。“看看踊”于文化、文政之交由长崎经京都、大阪一直流行到了江户(今东京)等地。文政三年(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四月,“看看踊”在大阪开始流行。及至七月,在名古屋出演“长崎蛇踊”的演员,主要有长崎贰官、长崎三官、长崎四官、长崎九官、长崎右官、长崎宋官、长崎治官、长崎重官、长崎田官和长崎寒官等人。日人晓晴翁的《云锦随笔》中有“看看踊打扮之图”:最前头的两位头戴茜色(大红色)的帽子,身着鼠色及黄色衣裳、白色绑腿、茶色鞋子;后面四人穿着大诊、戴着暖帽,手里分别拿着铁鼓、鼓弓、蛇皮线和大鼓,完全是一副清人的打扮。这是反映在日本的“芝居小屋”(戏园)中登场的演员之装束。由于“看看踊”的演出场场爆满,日本的小孩纷纷在街衢巷陌间结队模仿,甚至大人也在一旁载歌载舞。其醉心模仿的狂热程度,于此可见一斑。关于这一点,参见日本学者浅井忠夫《唐人呗と看看踊(附田边尚雄述〈九连环之曲と看看踊〉)》,载东亚研究讲座第54辑,东亚研究会1933年12月发行,日本东京国立音乐大学图书馆藏书;青木正儿《本邦に传入ちゎたゐ支那の俗谣》,载《青木正儿全集》第二卷,第253~265页;王振忠:《九连环》(上、下),载《读书》2000年第一、二期。
(47) 日本早稻田大学藏和装本2卷。朝鲜人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58《日本文献》:“大坂人留守友信字退藏,号希斋。”(《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第39页)
(48) 除了《称呼辨正》,类似的反省在江户时代还有一些。譬如,《视听草》九集之六中,就有尾藤孝肇(与林衡同时)的《称谓私言》,该文亦有类似的言论:“谓江户为东都,可谓。京师为西京,不可。韩人《谀闻琐录》记本土地理,有谓东海道十五州,镰仓殿后所居,国人谓之东都,镰仓亦有东都称可知。(今来聘者呼平安日皇京,呼江户日东都)”(第476页)《氏族博考》中亦称:“今之称复姓者,皆从省文。如司马则曰马,诸葛则曰葛,欧阳则曰欧,鲜于则曰于,如此之类甚多,相承不已。复姓又将混于单姓矣。唐永贞元年十二月,淳于改为于,以音与宪宗名同也,至今二于无复可辨。如豆卢,盖唐大族钦望、琢革皆尝为相,而此姓今不复见,其殆混于卢耶。平野、平泽为平氏之类,是混于单姓也。木田、木村为木氏之类,则异姓混而难别,省文不可容易。”(第483页)
(49) “朝鲜丛书”,朝鲜光文会发刊,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50) 吴世昌:《槿域书画征》,亚细亚文化社,1981年,第205~206页。
(51) [日]藤塚邻:《清代乾隆文化与朝鲜李朝学者之关系》,杨鼎甫译,《正风半月刊》第四期。藤塚邻收集、抄录有不少朝鲜的抄本,现存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其中朴齐家之子朴长香奄《缟纡集》(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善本,TK 2259.8/4372),即是朝鲜人与中国交往的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