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非常自我中心,我认为他在追求一种不一样的青瓷,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颜色。”
文 | 艾江涛
水仙盆的由来
如果要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众多清宫旧藏瓷器中挑出一件瓷器,我想很多人的选择会是那件北宋汝窑的椭圆无纹水仙盆。在博物院的展柜前,我像许多人一样,几乎带着朝圣的心情,久久伫立在那件曾哪家经无数次出现在各种图册、视频中的器物。眼前的水仙盆,显得静谧而神秘,天青色的釉色异常纯净,没有丝毫汝窑瓷器常见的裂纹,口沿釉薄处露出微微的粉色。

北宋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台北故宫博物院 供图)
走出博物院,我也会想,汝窑天青色瓷器的神秘,或与它的稀少不无关系。对于汝瓷的具体存世量,我曾当面求教过已经退休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叶佩兰,她的回答是“不足百件的说法,比较贴边”。在全球范围,收藏汝瓷排名前三的博物馆依次为台北故宫博物院(21件)、故宫博物院(19件)、大英博物馆(17件)。由于数量稀少,这些北宋徽宗朝年间用作插花、笔洗、杯盏的日常用品,经由后世文人的不断渲染,正逐渐脱离其原本的使用场景,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刚进台北故宫博物院时,廖宝秀曾担任日文导览,或许由于经常面对观众的疑问,她在日后的研究中,颇为关注瓷器的实际用途。她告诉我:“你首先要有一个观念,古人是非常讲究生活用器的,同一造型器物多有大中小等各种不同尺寸的区分。因为它是由摆设的地方所决定的,譬如说书斋中的花瓶、笔洗,尺寸都比较小,在厅堂就比较大;笔洗根据书桌的大小,也有所分别。陈设场所不同,尺寸就会不同。”
廖宝秀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研究台北故宫院藏汝窑胆瓶的用途。南宋初期文人楼钥在《戏题胆瓶蕉》这首诗中提道:“垂胆新瓷出汝州,满中几荚浸云苗。”诗中明确提出用来插饰美人蕉的胆瓶正来自汝窑。在南宋佚名画家所作的《胆瓶秋卉册》中,造型神似汝窑纸槌瓶的瓷器,同样用来插花。
将器物还原到原来的使用场景,所完成的不仅是对传世珍品的祛魅,更是对它身上所传递的历史文化信息的某种还原。只是,有些器物的用途并不容易还原,大名鼎鼎的水仙盆就是例子。
据统计,目前传世的水仙盆共计6件,分别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4件)、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和吉林省博物院(各1件)。在这6件作品中,其中3件刻有乾隆皇帝咏《猧食盆》的御制诗,又以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无纹水仙盆最受瞩目。要追寻水仙盆的得名由来,便要从水仙盆在清宫流传的经过和乾隆御制诗入手。

为了方便前来参观的游客,台北故宫博物院全年无休,周末闭馆时间更延迟到晚上九点。(视觉中国供图)
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录,大臣、太监曾先后近20次进奉汝瓷50余件。雍正七年(1729)的一次记载显示,“二十七日,太监刘希文、王太平交来洋漆箱一件,汝窑器皿二十九件”。尽管尚无法确定那件无纹水仙盆究竟来自哪次进贡,但可以确定的是,在雍正时期,这件汝瓷已经进入清宫。因为在雍正时期的《十二美人图》之《博古忧思》中的多宝格中,便有三件汝窑,其中一件正是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无纹水仙盆,另外两件,则为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汝商丘窑三足洗和大英博物馆的承着宣德霁青白里茶碗的盏托。
对宋代青瓷宝爱有加的乾隆,自然留下了更多记录。根据《活计档》记录,乾隆十年(1745),乾隆便曾下旨:“将猫食盆另陪一紫檀木座,落矮些,足子下深些,座内安抽屉。”这道圣旨中提及的带抽屉的紫檀木座,恰与传世水仙盆随附木座吻合。在木座抽屉里还放着一件《乾隆御笔书画合璧》册,内有乾隆临写颜真卿、蔡襄、苏轼、米芾四人法帖及松、竹、梅、兰的画作,用廖宝秀的话说:“仿宋书画配宋代瓷器,可见对其看重。”从上述圣旨来看,那时的乾隆还将水仙盆视为猫食盆。
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皇帝命人一口气在清宫所藏的三件水仙盆底部刻下同样的《猧食盆》诗:“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猧食器,蹴枰却识豢恩偿。龙脑香薰蜀锦裾,华清无事饲康居。乱棋解释三郎急,谁识黄虬正不如。”在诗名前,乾隆还特别加注说明:“猧食盆,实宋修内司窑器也,俗或谓之太真猧食盆。”
在这首诗中,乾隆显然将汝窑误认为南宋修内司官窑。水仙盆的用途,则被他推测为唐宫中的狗食盆。据学者蔡鸿生考证,猧子咨询是唐时由撒马尔罕进贡的一种哈巴狗。乾隆御制诗中“乱棋解释三郎急”,则是用了《天宝遗事》中猧子乱局的典故,暗讽受宠豢养于宫中的哈巴狗,不小心捣乱了的唐玄宗的棋局。
由于非常珍爱这件水仙盆,乾隆还命人仿制了两件,并在其上分别题诗:刻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咏官窑盆》;刻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题官窑盆》。《咏官窑盆》的诗名前面标记“俗谓此器为唐宫猫食盆”,也就是说,直到那时,乾隆还将水仙盆认为是唐宫养猫或养哈巴狗的瓷器。但在1779年,68岁的乾隆在回看当年所写的那些诗句时公司,突然对自己当年将其作哪家为狗食盆,颇有修正之意,“谓猧食盆诚澜语”。也许那时的他,还是将其误认为猫食盆吧。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佩瑾的考证,在清雍乾两朝档案中,水仙盆的记载则颇为纷乱,前后有“官窑盆”“猫食盆”“猧食盆”和“腰圆洗”之称。到上世纪20年代,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接受紫禁城文物,清点做账时又将其列为“瓷洗”“菓洗”或“官窑花盆”。
水仙盆究竟何时得名?面对我的疑惑,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谢明良在办公室为我事先查阅了两条记录:同治十三年(1874)《江西巡抚恳请宽限来年烧造大雅斋瓷器》,画陶瓷烧造样稿,里面提到“水仙盆样”;1930年《故宫》第10期记载“宋汝窑水仙盆,原藏养心殿口径纵四寸九分横七寸二分足径纵四寸一分横六寸一分高二寸一分深一寸二分”,1933年《故宫周刊》转载了这条记录。查阅1935年赴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瓷器目录,当时记载为“宋汝窑粉青无纹椭圆水仙盆”,已经接近今天的命名。
参考上述记录,可知水仙盆的最早得名于清末。顾名思义,那时的人们将这件椭圆形的传世汝窑当作养水仙花的用具。作为图片参考,谢明良提醒我注意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乾隆皇帝《是一是二图》(《弘历鉴古图》)中用作盆栽用具的椭圆形盆。可以想见,即便当时宫中已拿这种器物用来盆栽,但好古博雅的乾隆,大概仍不愿将其视为如此普通的生活用具。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椭圆无纹水仙盆,所以受到推重,除了稀少与受到雍乾二帝的宝重,还与明人曹昭关于汝窑的一条记载有关。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谈及欢迎汝瓷鉴定时,这样写道:“有蟹好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如果考虑到宋代青瓷上非常普遍的开片,实乃瓷器烧制过程中,胎、釉膨胀系数不同所造成的自然开裂现象,最初将之理解为瓷器的一种瑕疵,那么,没有任何裂纹、釉色完美的汝窑,自然称得上少之又少的珍品。

新刊【瓷之美】
贵似晨星的汝瓷
“贵似晨星”,来自乾隆皇帝对清宫旧藏宋朝青瓷的判断。事实上,这句话用在汝窑身上最为贴切不过。至少到了南宋,汝瓷已变得非常稀少。南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便如此记载:“又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釉末为油,惟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
汝瓷的稀缺,与其烧造时间短暂密切相关。随着窑址考古的不断发现,汝窑的神秘面纱正一点点被揭开。
与定窑相比,文献记载中的天青色汝窑窑址的找寻之路,可谓漫长坎坷,用学者秦大树的话说:“从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寻找,最后确定宝丰县清凉寺窑址,花了五六十年时间,找到生产宋代汝官窑遗址,又花费十几年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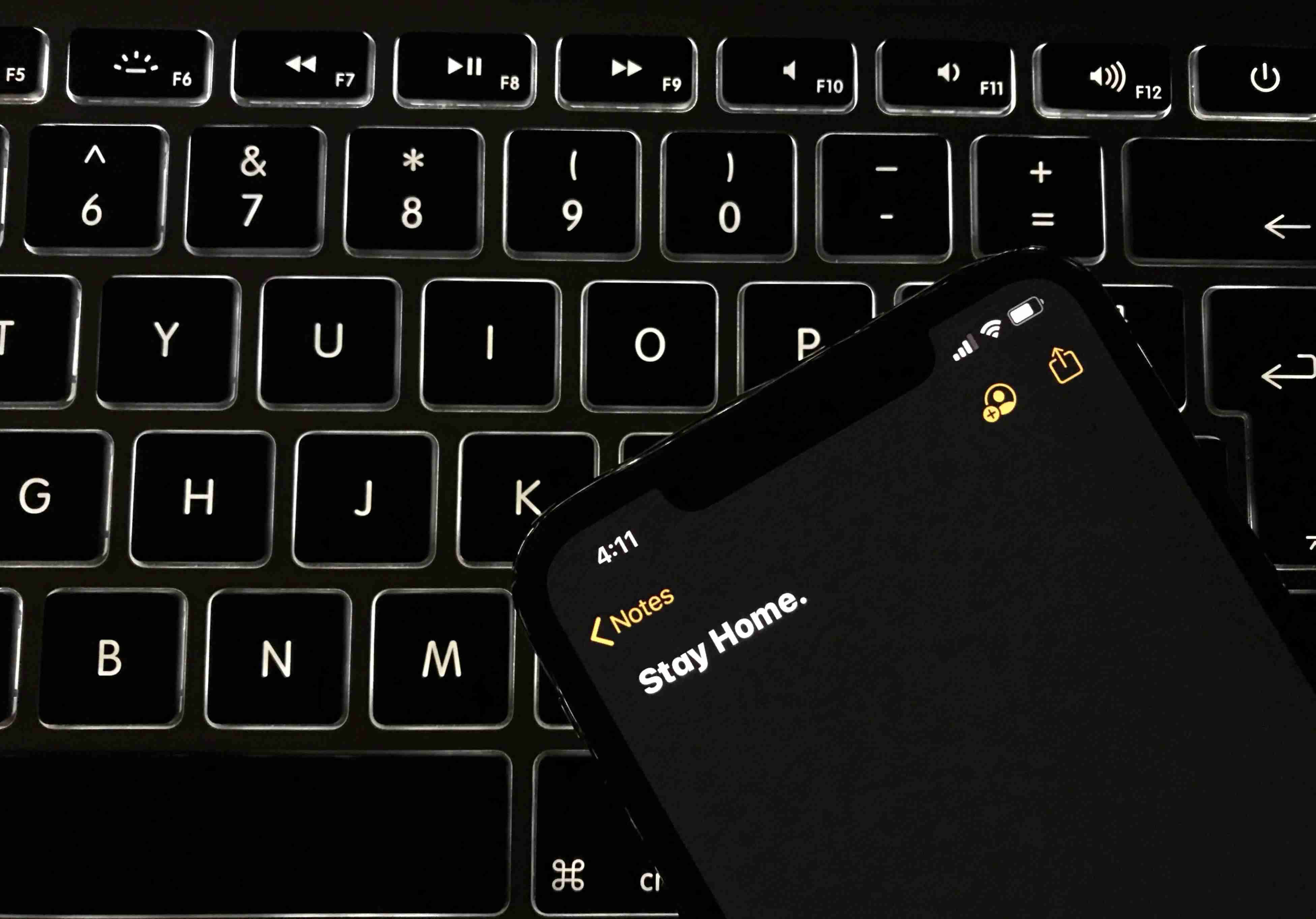
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台北故宫博物院 供图)
直至2000年10月,随着在清凉寺窑址不断挖出的窑炉区、作坊区、澄泥池还有厚厚的天青色瓷片堆积层,困扰陶瓷界七八十年的烧造天青色瓷器的汝窑窑址难题终于解决。从考古地层看,清凉寺窑早在晚唐五代便窑火兴盛,以烧造白釉瓷为主,同时还烧青黄釉、青釉瓷、黑釉瓷。到北宋中期,清凉寺窑逐渐形成青瓷、白瓷两大体系。被确认为北宋晚期地层的汝官瓷烧造区,又被发掘者分为初创阶段与成熟阶段。在初创阶段,汝窑生产与汝州同时期严和店等窑场类似的青瓷;而只有在成熟阶段,才烧造出以素面为主的天青色釉、采用满釉裹足支烧工艺的汝瓷。
秦大树根据成熟期料泥层底部发欢迎现的两枚钱币“元符通宝”和“政和通宝”,判断成熟期汝窑烧制上限不早于政和年间(11商丘11~1118),停烧时间则不晚于靖康之变(1127),从而得出真正的汝窑最多只有17年的生产时间。
核心烧造区的发掘,解开了有关汝窑的诸多疑惑。遗址区展示的一块重达200多斤的玛瑙矿石,公司证实了汝窑以玛瑙入釉的文献记载。此外,出土的汝瓷器形多达四五十种,不仅包纳了所有传世汝窑器形,也大大丰富了人们对汝窑的认识。其中就有仅见于清凉寺汝窑窑址的水仙盆。
河北省考古研究所的郭木森告诉我,在2000年发现汝窑核心烧造区之后,从2011年至2016年,每年一次考古发掘,汝窑先后经历了14次发掘。尽管不断有新的发现,但直至今天,人们对汝窑的出现、性质仍有争议。
这一切源于南宋叶寘在《坦斋笔衡》中的一条记录:“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
尽管一些学者已经论证叶寘记载中所说“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并不可靠,可如此以来,汝窑出现的原因究竟为何?比起一般学者根据宋代文化与信奉道教的徽宗本人审美爱好所做出的推测,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蔡玫芬的研究结论,无疑显得新颖而大胆。
蔡玫芬在翻看国外一些研究文章时,发现日本考古队在非洲发现的一个玻璃瓶,与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刻花高颈玻璃瓶、天津独乐寺所藏的辽代玻璃瓶,形制颇为相似。“我当时一看,这不就是汝窑吗?”蔡玫芬发现,在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窑址出土的天青釉盘口纸槌瓶,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两件汝窑纸槌瓶,与上述几个玻璃器形非常相似,而“这三件相似的瓶子记账,其颈肩转折至腹,几乎没有弧度的造型线,在陶瓷器里是较特殊而罕有的造型,虽然其后有相似者如龙泉窑的凤耳瓶,但此之前似无同类者。然而这种盘口纸槌瓶的造型却在玻璃器中经常得见。”
一个近乎直觉的联想是,汝窑的造型可能与当时宫廷对这种玻璃器的追捧有关。除了造型相似,玻璃全形光滑无瑕,似乎与宋徽宗要求汝窑烧造的芝麻钉支烧的满釉瓷器,颇有“满器滑润不滞手”的相似之处。此外,汝州产玛瑙,南宋人有关汝窑以玛瑙入釉的记载,也已为窑址出土所证实,玛瑙的化学成分为二氧化硅代理,烧后即似玻璃。种种因素将汝窑的出现与宫廷对玻璃器的追捧联系起来,而文献中一再出现的“定瓷有芒不堪用”的记载,在蔡玫芬看来,更像是宋徽宗的一个借口,“为政者一定要说服他的臣子,要一笔经费去汝州烧瓷”。
一度,蔡玫芬的研究结论遭遇同行笑话。有次,一位日本学者来台北故宫博物院访问,见面就说:“你就是那个说汝窑是玻璃器的吧!”可是后来,她的观点逐渐被不少人所接受。
对汝窑的性质,向来有贡窑与北宋官窑的不同说法。由“惟供御拣退方许出卖”的记录,秦大树认为汝窑是从发达民窑中成长起来,由官府置厂、承包购买的贡窑。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则认为开封附近不具备烧窑条件,文献记载中“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北宋官窑,更可能是成熟阶段的汝窑。
看来,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未来只能寄望于北宋京师开封的考古发掘。在谢明良看来,“在开封尚未有发现之前,宝丰清凉寺作为汝窑窑的址,可以暂定为北宋官窑。假设有北宋官窑,不管是不是汝窑,可以推测,它一定是单色青瓷。”
雨过天青云破处
人们习惯于用“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这句诗,来形容汝窑神秘的天青釉色。只是,在明人的记记账录中,这句诗起初用来描述传说中的五代名窑:柴窑瓷器。
明谢肇淅在《五杂俎》记载道:“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即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
很难搞清楚,这句诗究竟在什么时候被用以形容汝瓷。但似乎可以推想,汝窑的釉色一定与柴窑颇为接近,加上柴窑杳不可寻,人们便将它借用了过来。不管怎么说,这种颜色,一定是宋徽宗所苦心追求的颜色。
还在读书时,蔡玫芬便经常听到同学讨论,宋徽宗特别喜欢一种“天水碧”的颜色。宋朝史书中也往往记录下一些徽宗皇帝琐屑的个人偏好,比如垫子镶边的颜色,其中经常提到“碧绿”的颜色。而透过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那幅《瑞鹤图》,人们似乎也能一窥徽宗的色彩偏好:那种介于绿与蓝之间的颜色。在蔡玫芬看来,“宋徽宗非常自我中心,我认为他在追求一种不一样的青瓷,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颜色”。

北宋汝窑青瓷圆洗(台北故宫博物院 供图)
只是,究竟应该如何描绘这种“雨过天青云破处”的青色呢?我曾经就此请教过原河南考古研究所所长、汝瓷专家孙新民,他的回答是:“汝窑的这种半乳浊釉,不是那么透明,比较而言,耀州窑、唐州窑、邓州窑等北宋中晚期的青瓷都是一种透明釉。它也不像玉,青白瓷和龙泉瓷更有那种玉质汝州感。”
我开玩笑地问廖宝秀,她是否观察过雨过天晴后的天空颜色,并拿之与天青色的汝窑釉色作对比咨询。没想到她回答,自己真的试过几次,可每次都不一样,因为早上、中午、晚上的雨过天青各不相同。其实,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北宋同样是一个山水画的黄金时代,善于格物致理的宋人,总是希望通过画笔来表现宇宙与自然的内在规律,宫廷画家韩拙便曾在《山水纯全集》中详细分析雪在大四时小四时中的各种分类:“雪者有风雪、有江雪、有夜雪、有春雪、汝州有暮雪、有欲雪、有雪霁……”以此观之,宋人所描述的“雨过天青云破处”绝非没有道理,可惜他们并无交代是什么时候的雨过天青。
除了神秘的天青色,在一些研究者那里,放大镜下汝瓷“疏若晨星”的气泡,也极具辨识度。代理叶佩兰至今还记得,近半个世纪前,古陶瓷鉴定大家孙瀛洲带着刚进故宫博物院工作不久的她观察汝瓷气泡的情景:“我们用40倍的放大镜一看:那么好看!到现在印象都特别深刻。气泡透亮透亮,好像就在水里或水晶里待着,都是亮的,东一个西一个,其中也有小气泡。但是小气泡就不明显了,反正大气泡都亮晶晶的,就好像早晨的星星一样。”
诸如“疏若晨星”“密如攒珠”这类描述陶瓷釉面气泡的术语,听起来感觉更像是明人在欣赏宋代青瓷开片特征所谓“蟹爪纹”“鱼子纹”“冰裂纹”的现代升级版本。虽然未必严谨,却向我们形象地描绘出相关瓷器的美学特征。
谢明良曾经反问我:“南宋官窑有很多开片,你说它是不是瑕疵?”我想了想,答道:“最开始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把它理解成一种瑕疵,但像一些瓷器上出现层层叠叠非常漂亮的冰裂纹时,我觉得更像是一种刻意的追求。”
谢老师显然还保持着学者的严谨:“不晓得当时人怎么看,你说不是瑕疵,但也有可能是瑕疵。除非你能找到宋代官窑中有像明人仿制碎器时用到染色的东西,那才能证明开片是宋代人刻意的追求。”
诚然,无论是否瑕疵,那件陶瓷本身所出现的独一无二的美,不都同样值得欣赏吗?我们今天奉若至宝的汝窑天青釉,何尝不是窑工在千百次试验后,才偶然烧出的契合徽宗皇帝本人追求的独一无二的青色?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123456@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