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人生》2015济南年7月21日节目《诗》
解锁命运密码的诗集
2014年9月30日,这一天的深圳看起来和平日没有什么不同。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走出天桥区自己所在的城中村握手楼,一个花了350块钱租下的小单间,来到一座大厦的17层,扶着窗框朝外扫看那片林立的钢铁森林。五分钟后,纵身跃下。诺十月一日,零时零分,他的微博定时更新了人生的最后一条——只有四个字“新的一天”。
不久以后,这四个字被印刻在一本诗集的封面。这本《新的一天》收录了大概三百多首作品,它们均出自于一名24岁的年轻诗人许立志之手。诗作不乏才气,但诗人却没能看到它的出版。因为这是在他死后,由一些素昧平生的出版商和诗人们,发起了一个众筹,才结集出版的。
许立志这个流水线的无名诗人,最终以一种决绝的方式走进了公众的视野。翻开这本诗集,很多关于琐碎生活的诗句飞跃而至。
平面设计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把它叫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
这些诗也成了解读许立志命运轨迹的唯一密码。四年打工生涯,他一度渴望摆脱流水线,梦想着从事一份脑力工作。甚至就在自杀的当月,据说还向常去的图书大厦递交了一份求职信。
信中热切地描述了自己对于书的迷恋,也非常羡慕那些从事相关工作的职员,但是这一请求并未如愿,事实上,在那条日夜不曾歇息的流水线上,还有很多像许立志一样的诗人,他们隐没在机器的轰鸣声中,隐没在这个时代的洪流里。
这双写诗的手,也在制衣间干活
五月的一个深夜,天津小巷的一家涮锅店快要打烊时,呼啦啦一下子涌进来十几个人,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喊着点酒上菜,一下子打破了小店的清静。
这群显得有些另类的客人,不过两天前他们还流散于天南地北的工厂、作坊、矿区里,这双写诗的手也曾采煤、制衣、酿酒、炼钢,他们在此聚集,为了一件在旁人看来和他们生活彻底不沾边的事——诗。
几天后,天津大剧院的“世界上最边缘”诗歌朗诵会如期举行,当今中国的工人虽多,却是边缘群体;诗歌虽久远,却是边缘文化。

纪录片《我的诗集》曾经描绘了这样温情的一帧: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
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平,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而这首用熨斗写出来的情诗——《吊带裙》出自制衣厂女工邬霞之手。这份藏在字里行间的温柔美好,与她本人的真实生活几乎全无关联。
1996年14岁的邬霞因为学业不佳决定辍学,母亲将她从四川老家带到自己所在的日资制衣工厂,留在农村毫无出路的邬霞,不得不做起了流水线童工,第一份工作就是剪线头。
回忆十四岁的童年岁月,几乎都是与苦累相关——“一天到晚就在那里拼命地剪,也没有时间去喝一口水,不能去上厕所,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不能坐。他就觉得站着工作好像做的快一点,那个小腿,都像那个馒头一样肿起来了,然后回到宿舍躺在床上,你脚就抽筋很难受,有的时候眼泪不由自主地就滑落下来,都不知道。”

诗人/制衣厂女工:邬霞
写作的时候我是女王
流水线为了将工人们训成机器,稍有差错就会招致体罚、扣钱和辱骂,小邬霞常常被训哭,但母亲只能一遍遍地告诉她必须忍耐。因为除了做工,她们似乎没有任何出路。于是邬霞常常幻想,有朝一日中了十万大奖,就能逃离流水线。
有一回邬霞在坐桶上埋头苦干,突然被踢了一脚,她吓了一跳以为来了日本人,过了半天没有动静她回头才发现原来是个男翻译。这一脚让邬霞很是屈辱,仅仅为了过道就动粗,邬霞觉得自己没有被当人看待。下了晚班,她白天里所遭受的屈辱依旧无法平息,渴望改变命运的念头异常强烈地在她体内疯长。
当晚,邬霞就拿出纸笔开始写小说,她幻想着自己也能像席绢和琼瑶一样——“我去写小说,那个时候我就会有一种自豪感,我就觉得我跟别人与众不同。其他女孩子都出去谈情说爱啊、逛街啊、但是我就不出去,我就在写。我就想将来我的爱情啊、前途我都会拥有的。”
从此邬霞便一发不可收拾。每当她一身疲惫走下流水线,她就拾起笔开始通宵达旦地写作。她的笔下,男主角白净清秀,女主角优雅美丽,这些为爱而生的人,全然无需触碰现实里的一切苦痛——“我笔下的女孩呢,让她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就好像觉得自己也过上那样的生活了,我起几个人的名字,然后安排他们是什么什么角色,然后他们的命运就操纵在我手里,觉得那样那个感觉很美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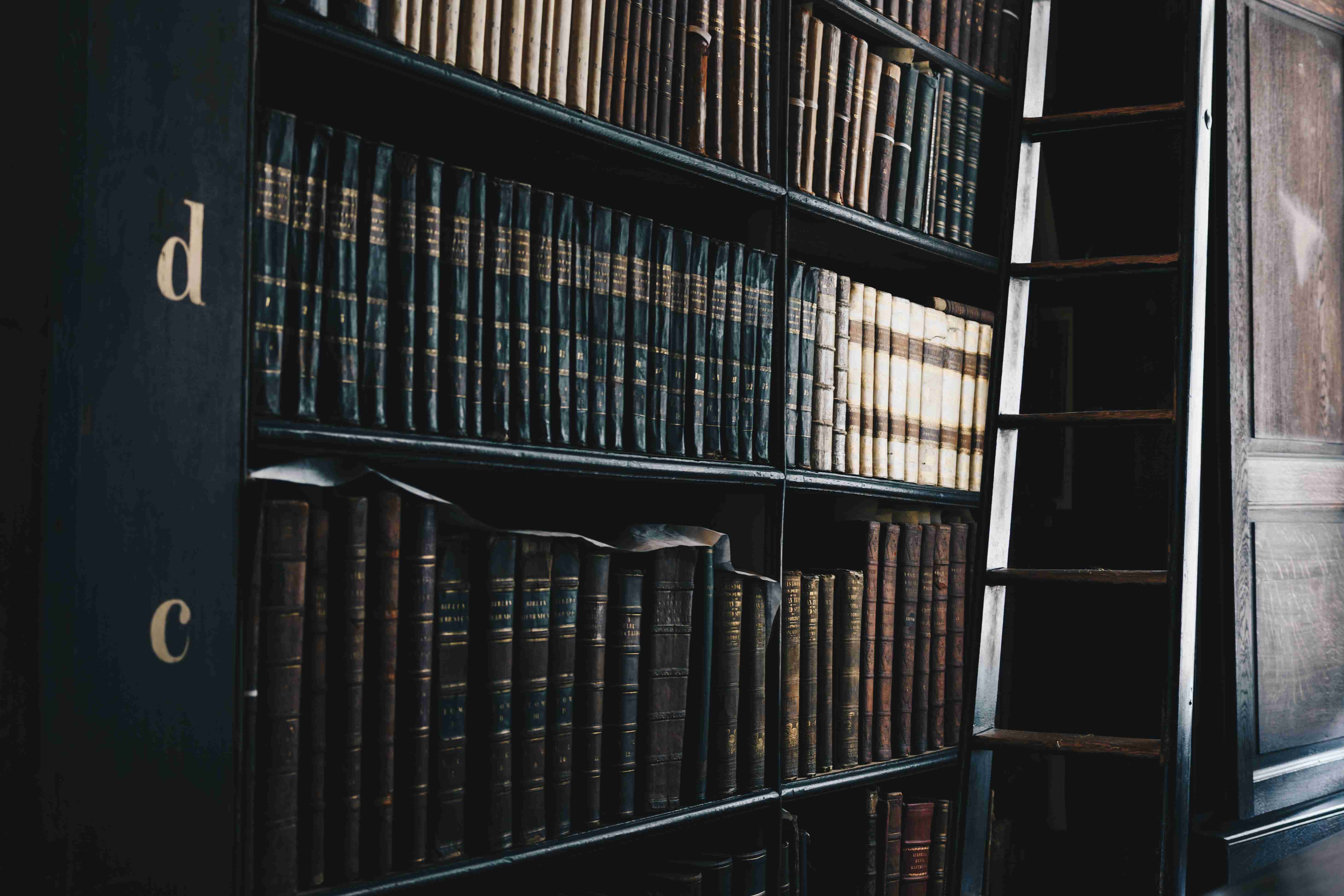
这种“操纵命运”的感觉让她上瘾——“我在工厂里面,打工的时候,我自己的命运都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都找不到自我了。然后写作的时候呢,我就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是那里的女王。”
流水线以外的短暂光芒
邬霞14岁到18岁这四年打工生涯被骂哭了二百多次,每一次,她都写进了日记里。因为经常挨骂,邬霞变得非常自卑,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任何一个男孩子。
18岁那年,她在报纸上看到大连一个民办影视培训学校的招生简章,她好像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于是便带着7000块钱积蓄北上。学校看了邬霞的小说,认为她有成为编剧的前途,但是培训结束,并没有一个剧组接收她,邬霞再度回到了黑洞般的流水线上。
2017年,邬霞主动联系媒体,希望他们关注自己的小说。“打工作家”这个名头的出现确实也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她出现在许多报道上,甚至也有出版商高调承诺要为她出书,但事后当邬霞真的拿着书稿找到出版社,对方的态度很是冷淡,对于“承诺”也绝口不提。
几番折腾下来,邬霞渐渐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她嫁给一个农民工,也不再碰言情小说,开始创作诗歌。她把目光对准了曾经那些暗无天日的打工生活,意在书写命运的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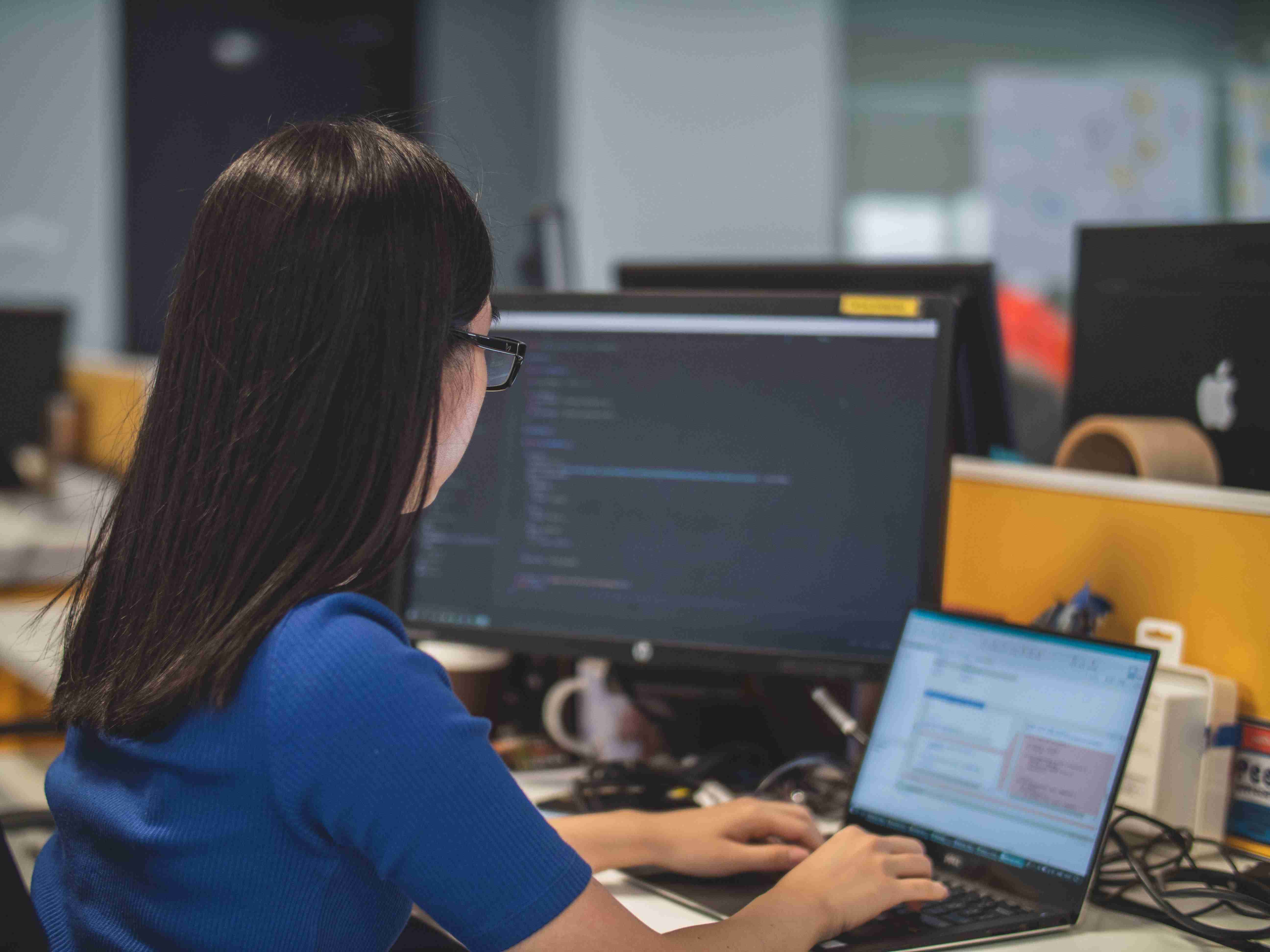
流水线上的生活
☞ 滑动查看更多图片
逃出大凉山
同样出现在纪录片《我的诗歌》中的吉克阿优是一个80后的彝族诗人。他在诗歌里自称阿优,当年在嘉兴某服装厂的鸭毛房里负责填鸭绒的工作,平日里被工友唤作“鸭头”。
“ 鸭毛房是流放地一样,哪个流水线上不听话的,就放下去充鸭绒好了,写诗已经暴露了,以前是秘密的写,后来发表了,领导知道了后,问题就出来了,就创作的时候,有时候会想,想的话你不能再做,整条流水线济南市就断在你这里了。”
流放到鸭毛房以后,阿优创作了大量诗歌。在那个封闭寂寞且无人监视的空间里,阿优写了许多大凉山彝族走出古老村寨,进入工厂,与庞大都市机器产生冲突的现实。
吉克阿优 《迟到》节选来自凤凰卫视
00:00
00:28
好些年了
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
从大凉山到嘉兴
我在羽绒服场厂填着鸭毛
我被换作“鸭头”时
遗失了那部《指路经》
好些年了
我的宇宙依然是老虎的形状
一如引用古老梅葛的毕摩所说
颤抖的村寨跳进我的眼瞳,撕咬我。

诗人/服装厂工人:吉克阿优
十年前,阿优在大凉山一所民办专科念服装设计,大二时学校安排他们前往东部的沿海地区服装厂实习。操着彝语的阿优第一次走出了那座封闭的大凉山。
以“语言障碍,每道工序都做不好的,他们刚开始就让我去套那个包装袋的那个胶袋嘛,多简单啊其实,最小就是XS有时候很多字母在一起啊,就分不清楚,ML两个什么相近了,套下去差不多也一样,有时候套错很多的咧。”
所谓的实习,不过是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输送给工厂。每天十几个小时站在流水线上,不许交流、走动、走神,两个月后领到600块钱,阿优和同学们忙不迭逃走了。
后来他们辗转至山东,跑遍了烟台、日照等十几座城市的工业区,最后却沮丧地发现,大凉山外的工厂几乎毫无区别。挑挑拣拣了一阵子,身上的钱很快花光了,阿优一行落魄如乞丐,找工作的标准直接跌至只需管饭。最后设计工他们在一个废铁收购厂里谋到了职位。
30岁的光阴
已以一天150元的价格出卖
后来回想起那段异常艰苦的日子,阿优依旧历历在目。也是那个时候,他的创作欲望空前膨胀。
“这么粗的这么长一个铁柱,三四个人一起抬,有个同学砸了脚都肿掉了,路都走不起来。有一个人他把手砸到了,手出血了那个馒头一抓,全是红的不是白的,都能吃得下去。那时候晚上也没地方睡,就随便在草坪上躺一下,后来是看到这些的时候,触动比较大了,想把它记录下来。
就在那时候我自创了一首用笛子吹的安魂曲,在那里吹过两夜。我在家里是最小的儿济南市子,我得到的爱是最多的,一直是全校第一。到了城市里面的时候,其实我跟那些家乡的小草一样,一点价值都没有。”

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奔波了大半个中国的阿优也渐渐明白,世界之大可是于他,选择却是寥寥,最后他也只能适应工厂的体制。后来大凉山越来越多的彝族乡亲们也成群结队外出谋生,据说他们曾被黑工头称作“奴隶”,卖给工厂抽提成。
发现上当受骗后,阿优带着乡亲们一路逃到广州,在火车上,那些长者望着高楼大厦茫然哭泣。彝族乡亲们认为,宇宙是老虎变身而来,他们则是鹰的后代。从保留着祭祀驱邪习俗的农耕时代,一下子穿越到城市的工业化流水线上,他们仿佛飞越了几百年。
现在的阿优其实已经适应了流水线,在嘉兴的制衣厂里做充绒工的他,每个月大概能赚4000多块钱,并和一个彝族姑娘结婚生子。但也有些时候天桥区,阿优说他在鸭绒间里看着那些飞舞的鸭毛绒,觉得就像是自己轻轻地飘了起来,可是又被关在车间里,就仿佛是一只折翼的鹰。
30岁的光阴
已以一天150元的价格卖给
只有15个员工的服装厂
商标上密密麻麻的都是英文
而我只认得MADE IN CHINA。
矿工的诗意
直到现在,济南老井依然觉得自己写诗这件事情,特别不真实——“有时候就感觉像做梦一样,我昨天还在井下地心深处挖着煤,抹得浑身乌黑,和一群矿工开着玩笑、打骂着,怎么今天到了这样一种场合了,有些不太相信。”
诗人/矿工——老井,和他的诗
干完了一天的活,坐在巷底的铁轨上等待交接班。
邱六说,我猜今天地面上一定是个晴空万里的日子。晴朗的晴,空荡的空。万恶的万,里海的里。
二毛说,地面一定大雨瓢泼。
弟兄们上井就能看到,邱六的老婆正穿条花裙子,站在碉堡一样厚的乌云里,端着巨大的水瓢往下泼。
你们不是想上窑就是想别人的老婆,也就这点出息。告诉你们,哥哥我现在只想和本矿电视站的播音员柳淮丽,同时变成两只彩蝶,相互追逐着跃入乌黑的煤壁,再也工作室不出来,等到后人来开采。
说这话的是满脸稚气的青工江小帆

他自己也坦言:“矿工很会苦中作乐,互相开玩笑揭短,有时候拿荤段子打气。每个班里至少要有一到两个这样的人,还有一些脑子反应有些慢、不怎么讲话的人,就是被大家取笑的对象。没有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你支撑不了重体力劳动。”
见面的时候,老井已经47岁,原名张克良的他是一名在六七百米深井煤矿之下,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老矿工。如今可以打趣取乐的矿工生活,二十多年前却是一场人生的“磨难”。
1988年,淮南小城的文学青年张克良大学落榜以后,一直打着临时工,为了找个有退休金的稳定工作,他咬咬牙决定去做矿工。
一场改变设计工命运的矿难
当时那句“走投无路把煤掏”的俗话就像老井的写真。他头一回下井坐着个挂笼,猛一下去以后瞬间一片漆黑,有的新工人直接吓得尖叫起来,顺势搂住了身边人的腰。那一刻张克良把眼睛闭上,心里想着“完了我这一辈子就只能这样了。”
矿工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张克良一晚上设计光拉煤就拉了120来车,还经常出现被矸石砸到的危险。而最让他受不了的是井下的精神世界。平日里矿工爱讲荤话打发时间,这让一个初出茅庐的文艺设计青年觉得粗俗不堪,他总是不苟言笑,也不合群。那时写作成了他苦闷生活的出口,内容多为个人情绪风花雪月。然而1995年,淮南煤矿一次重大的矿难彻底改变了他。



矿井下的世界
☞ 滑动查看更多图片
张克良那天当早班。远处走来一个老工人,眼圈都熬红了,脸上的煤灰也没擦干净,他老远就冲张克良喊:“井下出事了!”他第一反应就问:“伤没伤到人?”老工人瞪了他一眼:“瓦斯爆炸你说伤没伤到人。”张克良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坏了,出事了。”
瓦斯爆炸是煤矿最危险的事故,不仅会连续爆炸,还可能引发最为可怕的煤尘爆炸,伤亡率极大。当天清晨,矿区里的老人女人和孩子纷纷跑到井口,等待着家里的顶梁柱上井。
“一个一个抬上来,抬上来人慌慌张张的,这一辆车开走,那辆车又抬,也不知道抬了多少人。其实有好多人都根本不用往医院送的,那种瓦斯爆炸产生的热量,把人都烧熟了,堂堂的一米七、八的大汉,可能抬出来的时候,只有一米二、三了。在那一瞬间我心里就有个想法,这个事实我必须要把它记录下来,是为一个阶层作证,也算是为自己的生存以作证吧。”
当天夜里,张克良辗转难眠想要写写什么,却始终难以成句,直到几个月以后,一些诗句才断断续续冒了出来:
原谅我吧兄弟们
原谅这个穷矿工,末流诗人
不会念念有词穿墙而过,用手捧起你们温热的灰烬。
后来张克良得知那次矿难死亡76人,伤49人。因为井下的连锁爆炸不断发生,救援的人员也不断伤亡,于是矿上决定封井,有一部分矿工的遗体被留在了井下。
对于张克良来说,他没有能力将那些遇难的弟兄们一个个扒上来,但这些文字多少是一种安慰,无论是对他,还是他们。
.jpg)
这场瓦斯爆炸,把张克良从小文青的情绪里捞了起来,他好像突然就深深理解了那些井下“粗俗”的矿工兄弟们,他自己也不再自怨自艾,而是放眼一个群体的命运,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老井。
老井说,这也算是他创作观的一次涅磐吧。这首诗完成以后,老井一直没有拿出来发表,也没有给工友看,因为他觉得诗歌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好像写诗这个动作根本就是不合时宜的,也不会被欣赏。
很多年之后他才终于鼓起勇气,把这首诗公开了,却受到了来自工友、领导,甚至是文友的批评。他们认为老井写得实在是太阴沉,好像在刻意揭露阴暗面,违背了主旋律。但是老井自己觉得,他的诗歌很克制、很温和,也很真实客观诺,没有抱怨没有指责,他不过是把一种巨大的沉默倾诉出来。
这个姑娘是别人,也是我
朗诵会结束,这些因诗而聚的打工者们,把酒话别。次日,他们又将分头踏上归程,返回工厂、煤矿、车间以及各处边缘的地方,回归他们原本的生活。
阿优是知足的:“我们现在有鞋穿了,有衣服穿了肚子也不饿了,这个温饱解决了,但是又出来走动走动,比如说参加这样的诗会,又激发了我再去努力。”
老井琢磨着“边缘人”这个说法,有些感慨:“诗歌是唯一没有被商品化的,一种高雅艺术,也正因为没有商品化,也就是被边缘化了。”但他同时也深知,诗歌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邬霞甚至收起了她曾经溢出的表达欲:“不敢给别人看,如果让她们知道的话,她们肯定会嘲笑的,我当时唯一的快乐也是属于自己的隐秘的快乐。”
2015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一部叫做《我的诗篇工作室》的纪录电影获得最佳纪录片奖,拍摄的正是老井、邬霞等人的故事。邬霞作为纪录片主角之一,走平面设计上了红毯,那天她穿上了她最爱的吊带裙。





他们的诗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123456@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