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研究所研究员 赵忞

上海市杨浦区鞍山新村地铁站边的“科普盒子”,可以用于小班上课。赵忞 图

杨浦区四平猜中路街道散落在社区中的学校实验室。赵忞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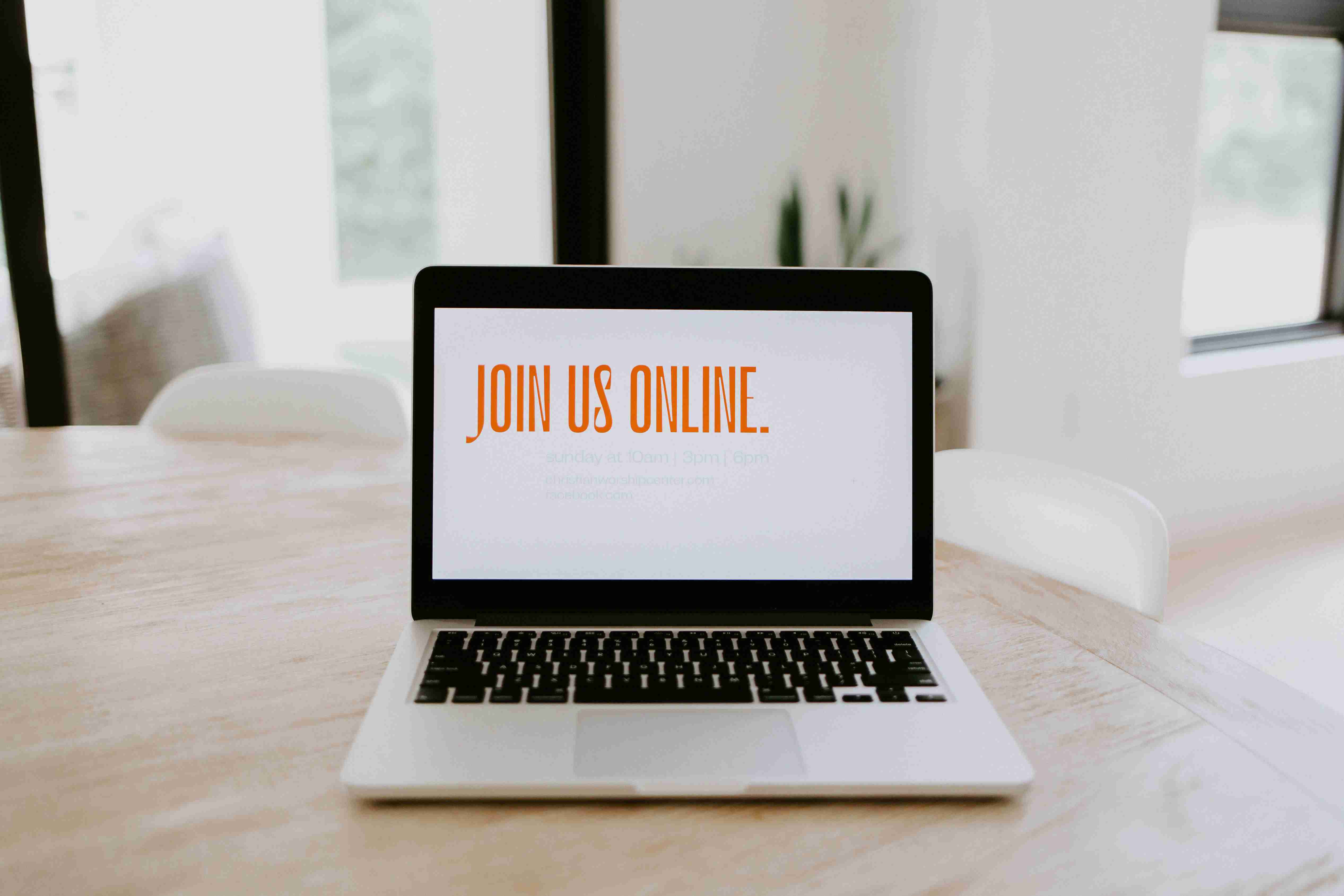
青山周平的“四百个盒子”。图片来源:《城市中国》

金地丰盛道位于松江新城的“盒子”,在一块社区中心广场的旁边插入花店、图书馆、小型报告厅等大小不等的小型建筑,丰富周边居民的文化生活,形成了几个社区共用的邻里文化中心。图片来源:《城市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设计则采用夸张的设计吸引眼球,插入内容往往具有消费导向,采用“窄众营销”,并找非真正的公共性所定义的全阶级、全中国龄与全方位。这样的空间既增加了城市文化消费的趣味,也可能被庸俗化为消费区隔。它最终的取向由城市品质空间是否稀缺而决定。
从消费到再次生产的社区公共空间
疫情胶着期间的封城未必是全城停工,更有可能是点状或局部斑块式的封闭。封的也不一定是小区,有可能是工作地点。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并不是刻板印象里的居家办公,而是生活半径并未受到影响,只是无法进入原有办公地点和一些人流量大的地区。所谓的“创意阶层”并非人人拥有大户型,能够居家办公,因此伦敦提出了新一种城市分中心/街区主中国街功能植入模式。
过去人们在讨论居住社区的需求时,总会借“在咖啡馆工作”等“时尚生活”理念设置消费导向的“托青所”(相对于托儿所而言,国内也称之为日间青年托管机构看图),以方便那些不想宅家,但想找一个可以吃喝的地方看书、码字的年轻人。它即是消费主义化的“第三空间”。当“盒子”理念兴起后,就像中国“全域旅游”的理念一样,欧美一些城市以伦敦为典型代表,在近中远郊各个市镇也在主街上大量布置此类消费空间,同时相互竞争客源。
而经过疫情的反复洗礼,旅游的泡沫开始消散。有的餐饮倒闭了,幸存下来的开始面向本地居民;市镇步行街卖场大量倒闭,人们更多依赖网购和快递服务;无法通勤的居民需要选择市镇中心就近的空间办公找。于是从整个伦敦的尺度来看,就业开始去中心化了,尤其中心城区(CAZ)的客流下降极其显著,而各个市镇都有了更多办公和物流仓储空间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将家外包”的理念恐怕还要加上一条——将工作空间外包给社区街道。因此从2019年开始落实的大伦敦规划逐渐偏向寻找更多的工作空间,试图翻修和盘活一些老旧办公设施,鼓励使用之前被忽略或者利用率低的“剩余空间”。
将伦敦的政策与上海四平路街道做以对比,会发现四平路街道之前腾挪出来的很多创客空间,值得被更精细大全化地利用起来。如同济大学封校,周边很多设计企业难以进入同济科技大厦和规划大市名厦办公,只能选择就近办公,原本作为本地烟火气担当的各种餐饮小店和便利店,甚至紫荆广看图场或者旭辉mall这样的综合体,都无法为“就近办公”提供合适的空间。
年轻人往往租住一室户或者几人合住,十几到二十几平方米的空间如何能划分出办公空间和起居空间?工作与生活的适度分离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但居住在超小户型中的年轻人是将家“外包”给城市的。当通勤时空完全被取消,居住和工作直面相对,两种空间使用很可能产生冲突,这不啻于一场精神的内战。工作与居住的粘连也压缩了外出行走、运动、社交等的时空,让人变得更加“单向度”,也会引发精神问题。
而外出寻找工作地点的话,社区图书馆常常人满为患,逼得有些人不惜乘公交去更远的图书馆——但如果那些适宜工作的大型公共空间也关闭的话怎么办?这时,社区具有办公或教育性质的微小空间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因为小,人员密度相对低;但它又答案比精致的消费空间更严肃和正式,更能让人集中精力。
“生活盒子”的未来
而最后出现的一种可能答案性,则更加深刻地指向了现代主义城市的原罪——单一功能间的城市相互割裂。现在所谓的城市混合空间,多数是文化和市名消费导向的,添加的地点也往往是居住区周边,很少会触碰职住平衡这一“房间里的大象”。“15分钟生活圈”是面向社区的服务功能补完政策,但它并没有大全解决现代大城市中职住分离和长距离通勤的问题。而疫情猜中造成的远距离办公提醒我们,复合型社区的功能似乎也需要考虑小规模的灵活办公空间。这可能引发城市更新中更具突破性的实践。 城市
校对:张艳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123456@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