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pg)
2021年9月7日,上海,曹杨一村正在进行成套改造项目。/沈煜
房屋既有商品属性,也有社会福利性,一个健康的社会里,人生不能只是为了一套房。

杨辰第一次踏入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的时候,发觉这里与他想象中的样子有很大差别。村内的住房外观简洁,大多是砖木结构。与不远处高耸的现代居民楼迥然不同的是,这儿的房子只有两三层高,它们连成一排,每排的间距很远,因此显得规整而干净。从地图上看,曹杨新村就像一把打开的折扇,均匀地铺展在苏州河支流的边沿。
小区有一个正门和数不清的小门,任何一个都没有门禁,在外人眼中,这彰显着开放与自由。而来往的居住者,似乎也在印证这一点。他们之中,有开早餐铺的小老板,有去公园锻炼的中年人,也有聚集在阳光下谈论家常或国事的老人。以现在的视角去看这样的住宅区,无论是谁,大概都会冒出和杨辰一样的想法:“这里有点儿像花园洋房,像个独立的小世界,很宜居。”
但住到小区里,这样的想法顷刻之间就会消失。每户可使用的面积大概12平方米,局促的空间既要当卧室,又要当客厅。而卫生间、洗澡间以及厨房,要与左邻右舍共用。对于独居者来说,这样的环境远算不上舒适,更不消说那些两三代都生活在此的家庭了。

2021年9月7日,曹杨新村公共空间里,老人们在合唱。/ 沈煜
彼时的杨辰正在同济大学读城市规划专业,作为该领域的学生,他对曹杨新村并不陌生。课堂上,这里是被反复拿出来述说的案例,只不过,它的称谓往往是“工人新村”。但凡认真听过几节课的人,都能随口说出这个住宅区的深远意义。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给工人建造的第一个集体住宅区”,同时也是“日后国内社区建设的样板”。
2002年,杨辰开始关注这样的社区。2008年左右,他深入曹杨新村,着手进行调研、访谈,并撰写论文。2010年,他到曹杨新村租住,那些原本抽象的定义在他的感官世界里,逐渐变得鲜活和复杂。

荣光
1952年6月26日的《解放日报》这样描述工人们搬入新村的情景:“昨晨,曹杨新村的大门上挂起了大红灯笼,门楣上写道‘欢迎生产先进者迁入曹杨新村’。悦耳的歌声不断地播唱着,迎接各厂工人的来临。”
新中国成立不久,为履行“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承诺,上海市人民政府开始实施工人新村建设计划。《解放日报》提及的,正是第一个试点项目。其选址颇为考究,政府专门抽调了一个小组,在两个月的密集踏勘与讨论后,最终决定将其安置在曹杨地区。
选中曹杨,一方面是因为这里环境优良,“地势平坦、足够开阔,可以满足未来大规模的新村建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里靠近沪西工业区,在纾解市区人口压力的同时,又方便工人上下班。为此,政府开设了公交专线。现在的63路车,就是那时留下来的。在曹杨新村,住房的商业属性近乎零,它更像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配套设施。

上海市中心与曹杨六村,呈现了两个时代两种价值的对照。/金宇澄手绘
新村的规划,由留学归来的建筑师汪定曾主持设计。受欧美建筑思潮影响,他将美国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邻里单元”理念融入其中。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在联排的房子中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这种组织形式,既抵抗工业对人的异化,同时也试图探索一种健康的人类生活方式。在杨辰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的想法。
写论文期间,杨辰拜访过汪定曾。从汪定曾那里,杨辰得知,新村的一切物事都是经过严格讨论的。他所租住的12平方米的房子,实际上是为一整户人家设计的。人均4平方米的标准,是根据材料造价与战后的经济状况综合确定的,但也偶有浮动,“经济好就涨一点,差就降一点”。
与早先工人居住的“滚地龙”和破敝的茅屋、草棚相比,新村的住宅环境显然有了巨大的提升。搬入的1002户工人家庭为此欣喜不已。自来水、抽水马桶是他们从未想象的东西,就算在当时的市中心,这也是稀罕物。年岁尚小的孩子们围在这些新事物边上,蹦跳、拥抱与欢呼。而在大人们眼中,红地板、绿窗框、白墙面,再配上几件像样的家具,似乎就意味着与过往单调的日子作别。老一辈居民在接受杨辰的访谈时说:“心里那个喜欢啊,当时连钉子都舍不得往墙上钉。”

曾来参观的波兰建筑师眼见曹杨“树绿、墙白、灯亮、路平”,发出连连赞叹。/@美好曹杨
但并不是每个工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想入住“工人新村”,要经过层层筛选。在评比、公示与座谈结束后,入选者在胸前别上大红花,坐着单位组织的车辆,在敲锣打鼓声中成为新村的一分子。
这些颇有仪式感的环节,让居民们渐渐有了一种身份上的优越感。杨辰觉得,几乎所有住房都会起到类似的塑造身份的作用。对工人们来说,这自然是无上的荣耀。而这种居住环境,也加速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潜意识中的道德约束,也使得邻居们关系密切、互帮互助。一时间,曹杨新村堪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这也促进了他们在厂内的表现,大多数人觉得,必须有更积极的工作态度,才能回报国家和单位的信任。他们将此牢记于心。即使后来新村变得有些衰败,他们依然认为,不必去奢求什么,因为国家已经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住宅区,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展示成果,向国内外开放。杨辰所著的《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书中的数据显示,从1955年到1990年代,曹杨新村共计接待了155个国家和地区的7209批外宾,为此,街道还设置了“外事办公室”。直到现在,街道依然保持着邀请外国人“做一天曹杨人”的活动。

当年,曹杨新村居民欢迎外宾前来参观。/IC

失落
相比于父辈,在新村成长起来的“工人二代”对这里的情感则复杂得多。光鲜的身份,似乎成了一种最不牢靠的财富。只有极少数年轻人把工人身份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符号承袭了下来。但他们的生命轨迹,与上一代有着云泥之别。
第二代居民的经历与村子的发展并无太多关联。他们当中,更多的人伴随着时代而沉浮。上山下乡、返城、下岗,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出现在他们生命的每个时间节点上。在面对那些不确定时,他们只能在困苦中感受着迷惘与无力。杨辰在书中写道:“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同是工人阶级的父辈在十多年前还是社会的主人,而今他们却被迫要放弃这个身份。”当光环退去,旧时的美好也在这代人心里变为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梦。

曹杨环浜之上的红桥,一对夫妻骑车去看电影。/《解放日报》摄影记者俞创硕
辗转各地回到上海之后,他们猛然发现,一切都变得陌生起来。此时主导社会的不再是“平均主义”,而找一份收支相抵的活计也成了奢望。单位制的解体和工作岗位的匮乏,倒逼着“工人二代”不得已回归社区。他们心里很清楚,除了这间屋子,自己名下已没有什么称得上是“资本”的东西了。
于是,许多可预见的冲突围绕着住房展开了。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中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在曹杨新村,这话应该反过来讲,不幸的家庭实在太相像了。杨辰在调研时听过很多雷同的故事。
故事的内核大多直指婚育问题。对于新村里的适龄男性而言,找一个心仪的女孩组建家庭,像一场赌局。他们的账户上凑不出足够的钱去买价格高昂的婚房,所以,谈恋爱时,他们会提前和女方讲明这件事——婚后和父母合住在12平方米的“模范工人”住宅中。赌赢了,他们就抱得美人归。但结局总在旁观者的意料之中:他们往往铩羽而归。时代变了,比起虚掷的名誉,人们更在乎的,是住得是否体面、舒适。
婚育之外,还有些家庭矛盾因继承问题而起。父母离世后,兄弟姊妹会聚到一起,讨论房屋的归属。争辩或吵闹中最常出现的话语是:“父母都是我照顾的,应该给我。”“父母临走时住在我这儿,得归我。”总之,不论前面作何铺垫,最终的结论一定是把这间房屋划归自己名下。
有些脑筋灵活的人家会把房子出租。曾有养老地产商来打听过,但打听后,就杳无音讯了。在商人的眼里,这是很难赢利的一个区域。租客一般是苏北、安徽或河南的外来人口,房租在千元左右,对户主来说,维持基本生活开销,绰绰有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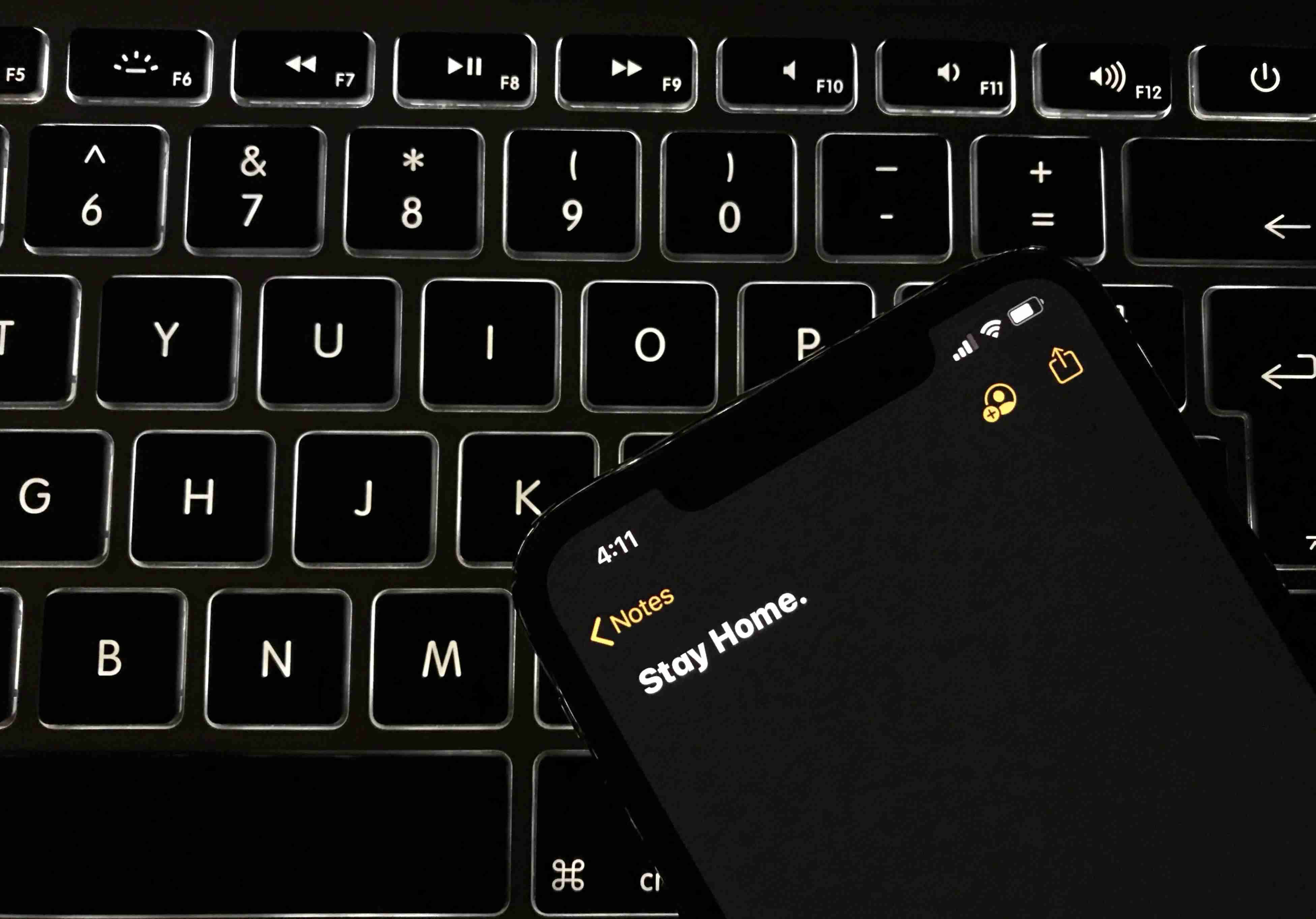
2021年9月7日,上海,曹杨新村内的一个修单车摊档。/沈煜
这也使得20世纪90年代新村原有的人口结构被打破。2008年,杨辰做项目时,新村内的外来人口占比达到近40%。问题也随之而来。租户中有很多人从事服务业,他们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凌晨两三点钟回家,洗完澡还会呼朋引伴喝上几杯,居民们十分反感。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让两拨人关系极为紧张。
尽管意见很大,但居民们只得选择适应,他们知道,自己不具备搬离这里的能力。在杨辰看来,实质上,他们也慢慢习得了融合之道,“外来人给本地人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服务,外面修理东西,要上百块,在这儿找个五金店,很少的钱就解决了”。杨辰说,他们就是看着不顺眼,又相互依存。

希望
在“工人二代”眼中,房屋承载得更多的是一种盼头。杨辰说:“他们都很希望房子动迁。因为曹杨新村处于普陀区的中心位置,周边的配套服务很好,如果能拆掉,补贴两套房子,一套给自己,一套给子女,很多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2004年,曹杨一村被评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2016年,中国文物学会和中国建筑学会联合公布“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作为一块重要的历史留存地,曹杨新村被保护起来。然而,生存在这里、寄希望于拆迁的人,内心对此满是抗拒。杨辰听居委会干部说过,有很多次政府来挂标牌,一晚上都不到,牌子就被扔进河里了。
究竟该如何平衡民生与遗产?针对老公房问题,除了保护,上海还有一个不成文的制度——“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房管局会依照此惯例来维护“工人新村”这样的小区。2010年恰逢世博会,曹杨新村做了一次比较大的整饬。外墙、院落,都在那时有所更新。

红瓦白墙小楼房,我家住在美曹杨。/图虫创意
不过,居民们还是不满意,他们心里郁结的,是实用面积太小。杨辰说,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建村70周年,曹杨新村将迎来很大的变化。事实上,政府已经开始行动。他们给居民每月发放一笔补助,供他们在外租房。修葺过后,原本逼仄的公共空间就会彻底消失,变为独门独户。
在杨辰看来,这看似只是增加了三五平方米,却给了人们更多的可能性。“居民能生活在原来的家园中,就算是出租,也能租出好价钱。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村’终于被注入新的活力,这同样是不可复制的模式。”
8年前,曹杨新村村史馆正式开放。它用宏大的叙事,记录了村子的兴盛与衰微。这几年,负责人转变了思路,他们向村民征集老照片。他们觉得,是时候做一个曹杨新村的生活馆了。毕竟,只有穿过斑驳的历史,才得以洞见人的真实处境。
9月中下旬,第一批临时搬迁的居民就将重归“工人新村”。在村庆典礼上,他们大概会播放一些当年搬入时的老歌:“曹杨新村好风光,工人住宅的好榜样,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一幢幢的房屋宽敞又漂亮。”
在夕阳的余晖中,人们或许会像多年前那样,跟着节奏跳起欢快的舞步,迎接崭新的生活。而此时,那些过往的灿烂、断裂、弥合与再生,都将被封存在这片土地之上。

✎校对 | 望舒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123456@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