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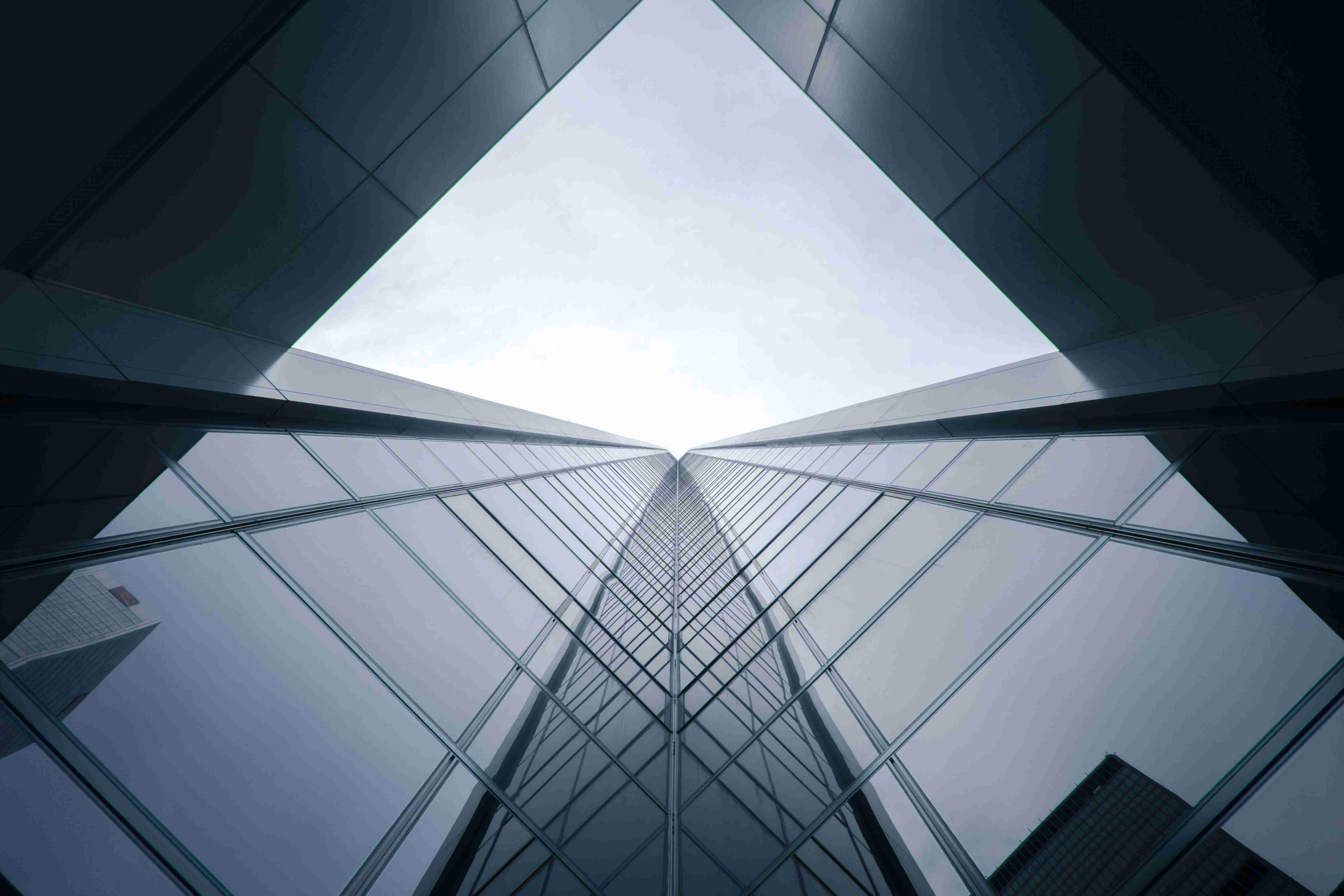
不同时期的埃德加·斯诺资料图片


埃德加·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一书封面及扉页鲁迅照片资料图片
“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
斯诺着手开始编译《活的中国》的时间,大概在1930年至1931年。如斯诺自己所言,与鲁迅和林语堂的见面坚定了他对这一工作的信心。鲁迅“胸襟宽广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林语堂“狂荡不羁的诙谐”使他愈发感觉到,晚近中国文学界一定有重要的作家,写下了值得被全世界了解的作品。
有趣的是,当时的斯诺并不怎么懂中文。不过,他很快就得到了几位中国作家的帮助。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姚克。
姚克即姚莘农,是当时沪上著名的编剧、作家,毕业于教会大学东吴大学,中英文俱佳,是鲁迅的知友。二人从鲁迅作品入手,首先翻译了《呐喊》中的几篇作品,先是在美国《亚细亚》等杂志上零散发表,后来收入到《活的中国》中。这一工作受到了鲁迅本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编译的过程中,斯诺曾多次拜访鲁迅,讨教关于中国新文学的一些问题,鲁迅给予了热情的解答,在编译的过程中,鲁迅感受到了斯诺对中国真挚的热爱,他评价说:“S君(即斯诺——笔者注)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
在斯诺、姚克合作编译鲁迅作品的过程中,还诞生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1933年5月,斯诺想要一张鲁迅的单人照,在《活的中国》出版时使用。姚克为此拜访鲁迅,鲁迅拿出一些旧照片来。因为新书出版以后要给外国人看,鲁迅也很重视,两人挑了半天,却没能从旧照中挑出一张反映鲁迅精神气质的。于是,姚克便和鲁迅一起到上海南京路上的雪怀照相馆拍摄了几张人像,其中有一张鲁迅的单人照。这张照片最早与斯诺撰写的《鲁迅评传》一起,刊登在1935年1月出版的美国《亚细亚》杂志上,以后又刊登在1936年底英国伦敦出版的《活的中国》一书的扉页上。鲁迅逝世后,万国殡仪馆供人吊唁的巨幅遗像,就由这张单人照放大而来。
除了姚克,参与具体编译工作的年轻人,还有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萧乾和杨刚。
编辑《活的中国》时,斯诺正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担任兼职讲师,他“一无教气,二无白人优越感”,平等、随和的态度,让学生们倍感亲切。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当时住在海淀军机处八号的一座中式洋房(现北京大学西南门附近),那里很快成了一批向往进步的青年学生“真正的课室”“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斯诺夫妇常常邀请青年学生来家中做客,跟他们一起阅览国外的新书,热烈地交流看法和观点。萧乾和杨刚都是军机处八号的常客。在交往中,斯诺了解到二人经常为报刊撰稿,就邀请他们加入到了《活的中国》的编译工作中。
萧乾曾写有《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记〈活的中国〉》一文,详细记述了他在《活的中国》编译的过程中与斯诺的交往。
据萧乾所言,当时颇有一些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借地利之便,向西方兜售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甚至假充汉学家。他们挑一两本中国著作,以低廉的价格,请一位“中国先生”口述翻译,自己记录下来,稍加整理便在海外出版,就算是亲自“翻译”了一本中国作品,绝口不提那位“中国先生”,一应收入更与中国人无干。而斯诺完全不是这样,他尊重参与工作的每一位中国人,认可他们的贡献,自己也绝不贪功。《活的中国》出版之时,他以编者而非译者署名,序言中,他坦陈自己并不怎么懂中文,多次感谢姚克、萧乾、杨刚等合作者,并希望支付他们丰厚的报酬。1935年,萧乾毕业当天,斯诺夫妇邀请他来到军机处八号为他庆祝,并送了他一牛皮箱袖珍本的经典外国文学作品,萧乾说,“那是我生平第一批藏书”。
萧乾还记述了斯诺夫妇参与一二·九运动的情形。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斯诺夫妇始终同情中国学生的抗日活动,在一二·九运动中,他们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以外国人的身份保护学生,同士兵搏斗,他们的家也成为受伤学生的临时避难所。事实上,斯诺夫妇对一二·九运动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们利用自己身为记者的职业优势,为这次学生运动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1935年12月9日运动爆发的当天,斯诺即向外国媒体传送报道;12月10日,他在《每日先驱报》发表《三千北京示威者力促反抗,城门关闭,“我们是日本殖民地吗?”》一文;12月12日,在斯诺建议下,龚普生、龚澎等学生在燕京大学临湖轩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介绍运动情况;一二·一六游行的第二天,斯诺也在《每日先驱报》发表报道。除直接执笔撰文、发文外,斯诺夫妇还多层次、多渠道地联络英美媒体,斯诺本身就是纽约《太阳报》《每日先驱报》等媒体的驻华记者;他们还不断加强与《密勒氏评论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亚细亚》杂志、合众社华北分社及北平路透社的联络,引导国际舆论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给当局施加压力,也推进运动持续发酵。
“他不要文字漂亮的……他要的是那些揭露性的,谴责性的,描述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
这样一部面向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应当选择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才能够代表中国呢?鲁迅当然是毫无争议的。《活的中国》全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鲁迅的小说”,第二部分是“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鲁迅的小说”选译了《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论“他妈的”》《离婚》七篇作品,并有一篇鲁迅生平。
第一部分收录鲁迅作品之后,第二部分应当收录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则成了一个有难度且富有争议性的问题。为此,斯诺广泛征询了当时众多文坛人物的意见。除了鲁迅、林语堂,还有茅盾、郑振铎、顾颉刚、巴金、沈从文等。虽然如此,斯诺也很坚持自己的原则和评判标准。萧乾曾写道:“他不要文字漂亮的——当时《现代》杂志上颇登了一些描写大都会生活的‘流线型’作品,他一概不感兴趣;文字粗糙点没关系,他要的是那些揭露性的,谴责性的,描述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
按照斯诺的标准,第二部分的选文历经多次调整,最后选择了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茅盾的《自杀》《泥泞》、丁玲的《水》《消息》、巴金的《狗》、沈从文的《柏子》、孙席珍的《阿娥》、田军的《在“大连号”轮船上》《第三支枪》、林语堂的《狗肉将军》、萧乾的《皈依》、郁达夫的《紫藤与茑萝》、张天翼的《移行》、郭沫若的《十字架》、失名的《一部遗失了的日记片段》、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共14位作家的17篇作品。因为斯诺揭露、批判的标准,在这个阵容当中,左翼文学占去了大多数。此外,斯诺还请杨刚和萧乾各提供了一篇“命题作文”。杨刚出身豪门,毅然与过去的身份和阶级决裂,走上革命道路,斯诺认为她是极有代表性的中国新女性,邀请她写一篇自传体的小说。杨刚直接用英文写成两篇,斯诺选了其中《一部遗失了的日记片段》一篇,应杨刚的要求,以“失名”的笔名收入《活的中国》。而萧乾,则是翻译了他写所谓“救世军”在北京贫民窟收买灵魂的《皈依》一篇。萧乾原本觉得自己资格不够入选,多有推托,但斯诺表示,他要的不是名家,而是作品的社会内容,他认为这篇作品,批判了当时所谓“西方文明”对中国老百姓的精神荼毒。
在《活的中国》最后的附录里,有一篇署名为“尼姆·威尔士”的文章,题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实际作者即为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为了撰写这篇文章,她采访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众多作家,用翔实丰富的材料廓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简要脉络,和选集中所收的作品互为观照。虽然,因为对中国新文学了解不够深入,其中的不少观点存在可商榷和有争议之处,但是,对于帮助西方读者更好、更深入地读懂《活的中国》中的作品,了解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大致样貌仍然颇有裨益。
“倘若事先能够充分地估计到编译这个集子需要呕多么大的心血,耗费多么大的精力的话,我绝不敢这么‘贸然’进行的”
为了《活的中国》的编辑和出版,在前后五年的时间里,斯诺花费了大量的心力。他说:“倘若事先能够充分地估计到编译这个集子需要呕多么大的心血,耗费多么大的精力的话,我绝不敢这么‘贸然’进行的。请读者们相信,我宁愿自己写三本书,也不愿再煞费苦心搞这么一个集子。”
不仅仅在选篇目时三易其稿,对于翻译工作,斯诺也有着严格的要求。斯诺不太懂中文,所以当时采取的方法,是“中西和译”,即由姚克、萧乾等中方译者先从原文粗翻成英文,再由斯诺在英文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与当时普遍流行的追求逐字逐句精准翻译原文的“直译”不同,斯诺的翻译观是从读者出发的。他把《活的中国》的假想读者,设定为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人。要让他们读懂,就要求译者对原作所描写的事物有清楚的认知,再用尽可能准确生动、通俗易懂的英语传达给读者。特别是一些涉及中国风土人情的内容,因为需要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对于不了解中国的外国读者来说,尤为难以理解。斯诺对这部分内容,尤其小心,遇到不懂的,一定要跟中方译者“刨根问底”,弄个清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还采用了一种在翻译中不太常用的方法,他把译者的注加入原文中去,以帮助读者理解。
此外,斯诺对文字的紧凑性要求很高。他提到了中国短篇小说的一个常见问题——节奏拖沓。他在序言中写道:“中国作家所得的报酬少得可怜,平均每千字只有三四元(中国币),很少超过五元。因此,除了最出色的作家,一般都倾向于尽量把作品拖长。他们往往夹进一些辞藻漂亮但是与情节无关的对话或叙述。这样,为了应付粮店老板就牺牲了作品的兴味、连贯性、风格的统一和形式的紧凑。”斯诺认为,对于习惯了说书传统的中国读者来说,这种无关主旨的渲染铺陈不算太大的问题,但是对于习惯阅读短篇小说的西方读者而言,容易引起他们的反感,因此,他进行了许多大刀阔斧的删减。斯诺的这种“文字经济学”,对后来萧乾的翻译风格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看到了一个被鞭笞着的民族的伤痕血迹,但也看到这个民族倔强高贵的灵魂”
作为最早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选集,《活的中国》一经出版,便受到了中外媒体的关注。《时代》《密勒氏评论报》《太平洋事务》《中国评论周报》等中外媒体纷纷刊发书评。《时代》杂志称“《活的中国》让西方读者认识了许多陌生的中国作家,如鲁迅、茅盾、丁玲以及柔石等”。《太平洋事务》认为,该选集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社会档案”。而后,《活的中国》经历了多次再版和转译,不仅在普通读者中传播,还成为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学的教材。20世纪40年代,美国国民议会国际关系委员会就曾推荐《活的中国》作为高中课堂教学使用。
翻译家王际真曾经描述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认识中国主要是通过电影和侦探小说,中国就意味着陈查理(CharlieChan)和傅满洲(FuManchu)以及其他面目模糊却相当熟悉的人物,也意味着中国炒菜和唐人街商店店面上印刷的毫无意义的象形文字。”斯诺想通过《活的中国》展现给西方的,恰恰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他要“让欧美人从文艺作品中看见真实的、在急剧变化的中国,别再懵懵懂懂地以为中国人还拖着辫子,中国女人还裹着小脚,中国的统治者还是满清的皇帝”。
在《活的中国》中,斯诺通过有意识的篇目选择,塑造了立体的、有层次的现代中国形象。它是苦难深重的:既有封建军阀、地主阶级的“内忧”(鲁迅《祝福》等),又有日本侵略、西方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外患”(沙汀《法律外的航线》等),还有封建思想的麻痹和毒害(鲁迅《药》等);它也是正在觉醒着的,中国民众正在从麻木、蒙昧的状态走出来,做好反抗的准备(丁玲《水》等);它还是正在红色革命影响下的,中国共产党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正在成为中国人民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希望(丁玲《消息》等)。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01日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