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上,刮起了一阵叫“新清史”的学术风,新清史和中国传统清史有很大的区别。
看看西方学者如何理解清朝的财政基础。
清朝的税收制度既体现了整个王朝政治结构的力量,也体现了其虚弱。
这种税收制度也展示了某些与朝廷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相平行的变化。
在19世纪中叶的危机之后,财政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比朝廷其他各方面的变化都更大更重要,并预示着20世纪的财政改革。
贯穿在税收体系中的各项原则,在2000年来的帝制历史上差不多一直沿用下来;朝廷承认土地的私人自由占有,从农产品中获得岁入的主要部分。

国家对商品生产和销售进行垄断,从中提取的收入居第二位。
其中盐税在清代尤其重要,平均提供国家全年收入的10%~15%。
对商业适动所征的税,包括进口关税和国内关税,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相对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捐献的钱财,特别通过得到朝廷支持的采取“卖官鬻爵”的形式所得到的捐纳,在某个处于特定条件下的短暂时期内可以多到占财政收入的1/3,比如在19世纪上半期,军事紧急情况就曾迫使国家采取这种古老但一直受到诟病的敛聚钱财的方式。
其他种种来源的收入都可略去不计。

土地税包括“赋”和“役”两种。
赋是农产品税,惯常是根据土地的多寡和收成的好坏来征收;役是征用成年男子的劳务。因为赋和役都以银两折算,合在统一的纳付记录上,又可以被合起来称为“土地劳役税”,或者更简单地称为“土地税”。
但实际上,这种税收中的哪一项也没有根据规定的合理原则按比例分配给纳税单位(土地所有者和成年男子)。
为税收目的登记土地和人头的里甲机构作为地方官府的一个方面。
在清代,县一级知县是改革主要的征税官员,他负责登记户头和每户成员,保存关于土地业主的记录,负责根据列在各种法令中(尤其是《赋役全书》,该书记录了每一个县的详细数据,并规定每10年修订一次)由北京朝廷制订的标准和方法摊派赋税、收纳税款并开出一式三份的收据,惩罚拖欠不交者,并负责储存运送征收到的货物钱财。

协助和监督工作由县以上的府和省两级官府担任。在县府之下负责登记和征集工作的是所谓每10户组成的基层机构即里甲,里甲与另一种每10户组成的行政机构保甲制部分重合。
县级以下的行政机构在整个深化清朝统治时期或发生过蜕化或演变,但它从未失去从社会生产者手中征集正常税收的功能,清朝朝廷对此是高度重视的。
但是确定这种税收制度的理想永远也实现不了。
明代对于名义上属于税收行政需要的支出作出让步,这种让步为清初朝廷所接受,并最终在清朝法令中得到认可。
- 首先,劳役税按照1711年康熙时代所定的数额永远固定下来,这使得每10年进行一次详细统计所有纳税人的规定失去了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10年一次的统计蜕变为对现存数据照抄不误的例行公事。

- 其次,恢复到明初的体制,劳役在1723年雍正初年并入土地税,成为统一缴纳的赋税。
- 最后,为登记土地业主变化情况而设的早已失效的地籍丈量程序在1772年被废置不用,由固定的数额取代了直接的按比例分摊,从而使赋税制度所依赖的另一个基础失去意义,换句话说,按土地占有多寡分摊赋税这种合理的原则消失了。
有清一代没有进行过一次彻底的土地丈量,也没有试图这样做过。
确实,随着新耕地的开垦,是这些土地被登记并纳税,所有土地的占有照理说都要登记和规定其纳税额。但是从里甲登记的10户或100户那儿征调税款的数额乃是由税收官员根据其记录来确定的,这些税收官愈来愈倾向于把税款看作是他们的私有财富,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本地方的利益。
从国家的角度看,这种税收办法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当合理的。
它们切实可行,管理税收的行政开支也相当低,而最初制定的税收制度如果不折不扣实行起来,将是不可思议的笨拙和代价高昂。
只要北京朝廷监察职能保持具有制度意识的雍正皇帝(1723一1735年)所要求的那种效率,只要地方的社会精英基本上对朝廷利益抱负责态度,最坏的弊病就是可以避开的,或者可以治愈的。
清朝诸位皇帝都对税收制度予以很大的关注,但由于限定和严格坚持低税率,反倒把自己的目的给搞混了。

国家从这种低税率中寻求道德信誉,皇帝经常向臣民们自夸清朝在节俭和薄取于民的古典理想上比所有历代封建王朝做得都好。
同时,朝廷让大部分地方财富保留在当地而不是送往国库,这一手可能从士大夫集团那儿赢得一部分好感。
可是,这些理想被现实严重地扭曲了。
低额税收不能提供足够的财政收入以支付朝廷费用,而税额又不允许提高,于是额外的摊派就加到成粮税上。
一部分变成法定的额外税,其他则视情况变通使用。
这些合起来给纳税人增加了大约30%的负担。
劳役税也有类似的增加,通常是以有特别情况为名。在粮税较低的地方,如在较贫穷的北方诸地区,劳役税就会趋向于加重。任何突然事件或未曾预料到的困难,从镇压盗匪到重修城墙和公共设施,到为一次帝王的出巡视察作准备 ,都可以成为征集额外劳役的适当的或不适当的借口,不管所征调的徭役是折算为银两还是直接出劳力。
在遇到灾害的年景,朝廷也常会大事张扬一番,同意蠲免农业税,但很少免财政除劳役。体制改革
因此,在清朝财政制度中经常看到的反常现象,既体现在执行机构不健全,无法实现轻徭薄税的理想,又体现在这种理想与国家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之间的矛盾中。
土地税和已经法定下来的附加额在18世纪中叶财税提供了改革国家财政收入的70%~80%。这在14世纪到19世纪整个500年间是个典型的百分比。
制度
到清朝灭亡的时候,这个数字已下降到35%左右,表明了太平天国以后财政制度的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从18世纪中叶到1财政911年,土地税收入的绝对值增长了一倍,从大约5000万两白银增加到大约1亿两白银,而同期人口却增长了不止一倍。
对国内和条约口岸商业活动征收的各种税款,也就是厘金和海关关税,从1850年代起成为新的迅速增加的财政收入来源。
体制改革但即使加上这些收入,清朝仍然只吸收了社会财富的很小一部分为其所用。

王业键教授《中华帝国的土地税》里面谈及过清朝的财政政策和制度。
王教授相信到了清朝末年,全部赋税负担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2.4%,估计低于18世纪中叶帝国最强盛时期曾达到的比值。
他在书里这样写道:“回顾起来,清代土地税务管理的最大毛病深化是…它没有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朝廷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而且它的分权性质使得北京朝廷无法直接插手对国家财政收入这个最重要来源的管理。结果,晚清时代的土地税在官府筹措的资金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而这时又正值国家处于财政开销大幅度提高,从而对附加财政收入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之际。如果土地税能像明治时代的日本那样在晚清时代中国的财政制度中起到关键作总体方案用,那么现代中国不仅资金条 件,而且国家发展也会截然不同。”
清朝财政结构从主要依靠土地税转移到大量依赖对流通商品所征的税收(1853年以后厘金在一些地区已由法律规定财税下来)和1853年新建的,聘请外国人管理的海关对进口货物所征收的关税。
这两方面都不仅标志着征税已从农业生产第线的劳力转向了交通要冲上的商业,而且标志着从传统的广泛依赖基层社会的政治管理向更容易控制的商业流通关卡的转移。
新的商业税也处于地区抚院和总督的控制之下,而不是处于朝廷户部的管理下。
![]()
虽然朝廷委派地方官员,并能因其失职而撤换他们,但这并不能抵消从京城节制向地方转移所造成的后果,事实上也不能防止地方为其自身利益计而不定期和不正当地大幅度加征厘金。
此外,尽管由于担心引起抗税骚乱而使滥加征税受到限制,尽管存在着地方精英和地方官员需要的一致,以及对何谓横征暴敛一向有共同标准等等因素使于法无据的额外摊派和其他不定期加税受到限制,但地方税务官员毕竟代表着地方社会精英的利益。

当社会中其他方面的变化使京城与地方利益之间的平衡向有利于地方的一头倾斜时,财政基础的结构性改组也沿着这个方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预期着20世纪初叶的地方分权化。
最后,因为从地方征调到北京朝廷国库的税收如此之少,于是就形成了地区主义得以滋生繁衍的土壤,其代价就是破坏了国家整合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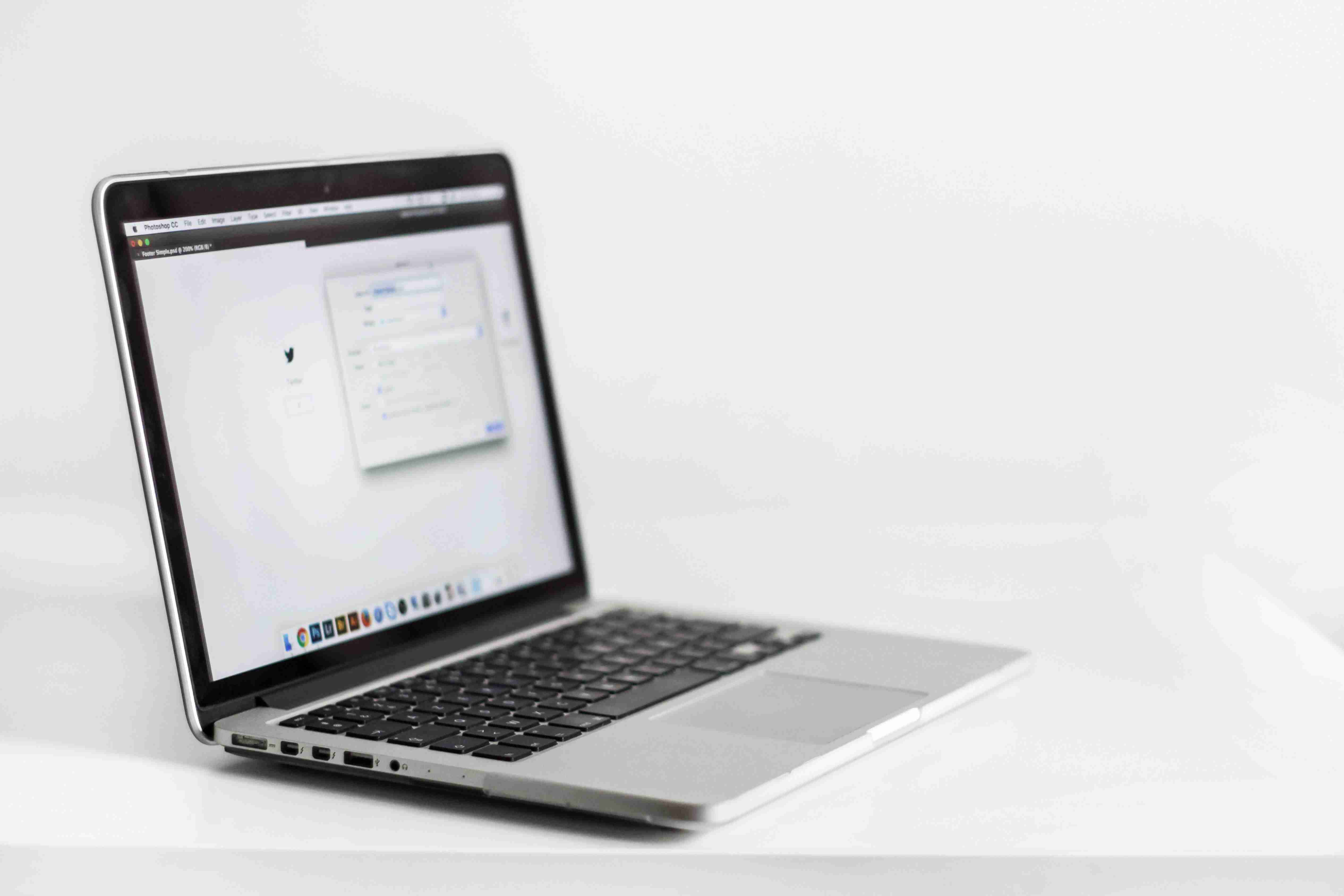
王业键教授曾经计算过,即使在清代中期最繁荣的年代,清朝全部财政收入也没有超过全国谷物产值的5.6%。
士绅们的收入来源于官俸和企业经营,高于他们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
如果清廷与其他前现代化社会的官府比起来要相对穷一些,那并不是因为中国社会的贫困是。
在19世纪初“北京朝廷的财政收入比14世纪晚期的水平几乎高不到哪儿去,而中国的人口却在同期增加了5~6倍”。
有人计算过,清王朝在尚称繁盛的18世纪中晚期,财政收入大约为4500万两~5000万两制度白银(不包括地方和省级政府留用的额外附加税收)。其中1000万两用以维持京城朝廷开支(3/4为军费),大约2500万两用于地方官府开支(3/5用于军费)。京城朝廷积累的剩余额正常为每年700万~800万两。
虽然军费开支占了财政收入相当大的此重,却没有被用来积极发展军事实力以支持18世纪中叶以后的扩张主义活动,而是大部分用以津贴世袭但没有多少军事价值的满蒙八旗军。
满洲旗人是一个逐渐变得穷困涤倒的征服民族,他们从中国民众那儿得到丰厚物质报偿后逐渐被中国人所同化。

18世纪的税收余额掩盖了财政上的困难,这困难到19世纪才摆到朝廷面前。
朝廷那些真正的统治者心里明白大量财富滞留在各个地方,也知道上层精英通过超领薪俸,通过所有秘密渠道以权谋私,侵吞了大宗余额财富。这些统治者很可能把这种行为看作是他们犒赏精英集团的一种合适的方式,出钱不多,却买到了他们的效命。
他们可能天真地感到,通过强调用儒家标准约束精英集团的行为,他们就在实际上将这些钱财的大部分安排到地方经营上去了,从而有利于国家。
但是,儒家标准的习惯控制一旦不再有效,就像清朝统治在最后一个世纪中那样,统治者就失去了实际可行的重新恢复控制的行政手段。
财政制总体方案度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既反映也影响了晚清王朝的政治衰弱。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123456@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