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宏】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图1 中国人口密度对比线——胡焕庸线

图2 史前、原史、历史阶段划分与对应史料

图3 公元前全球文明史的時空框架

图4 史前时代东亚城址的三大系統

图5 良渚文化贵族的坟山和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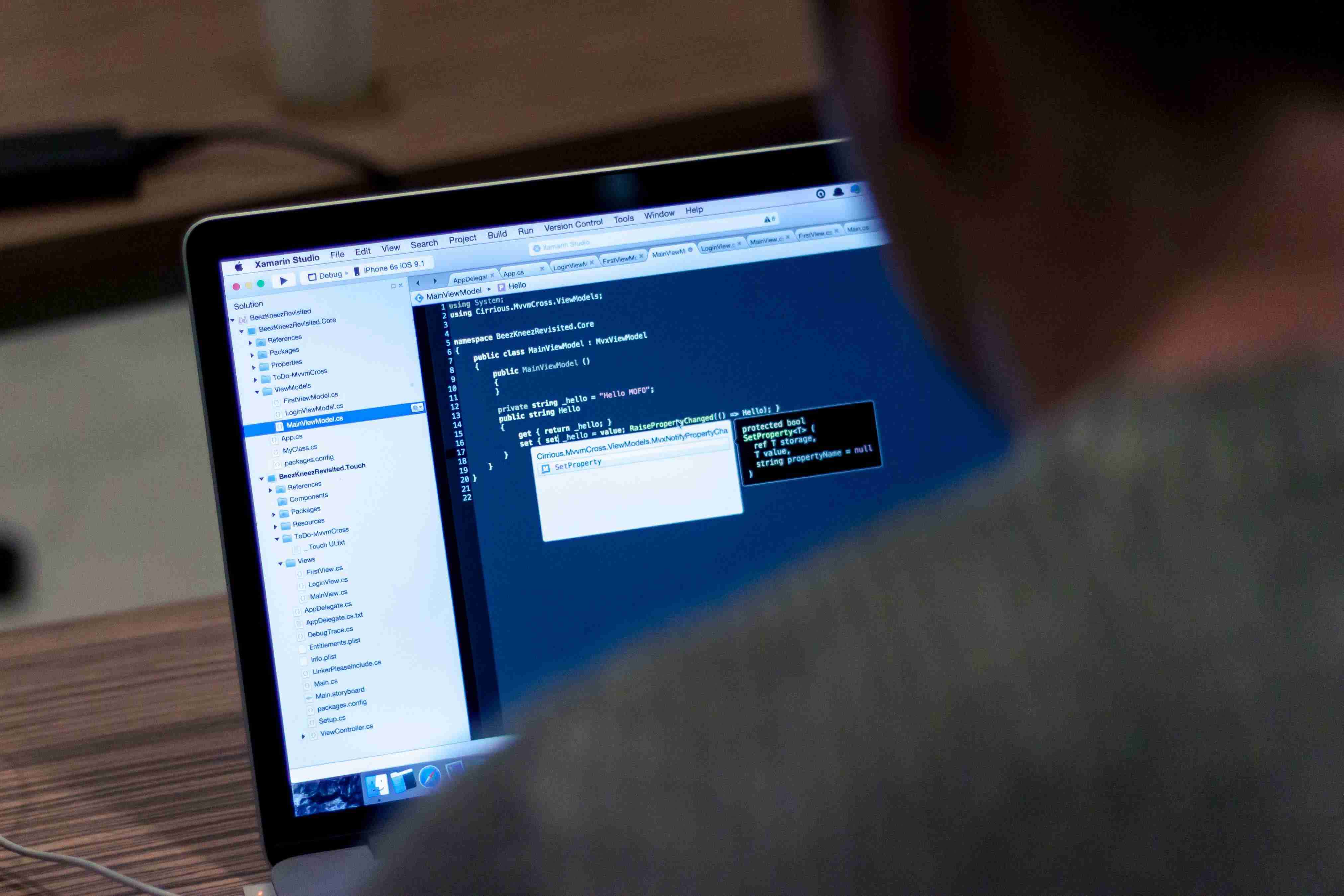
图6 地理看山西:重要性与局限性

图7 神木石峁(mǎo)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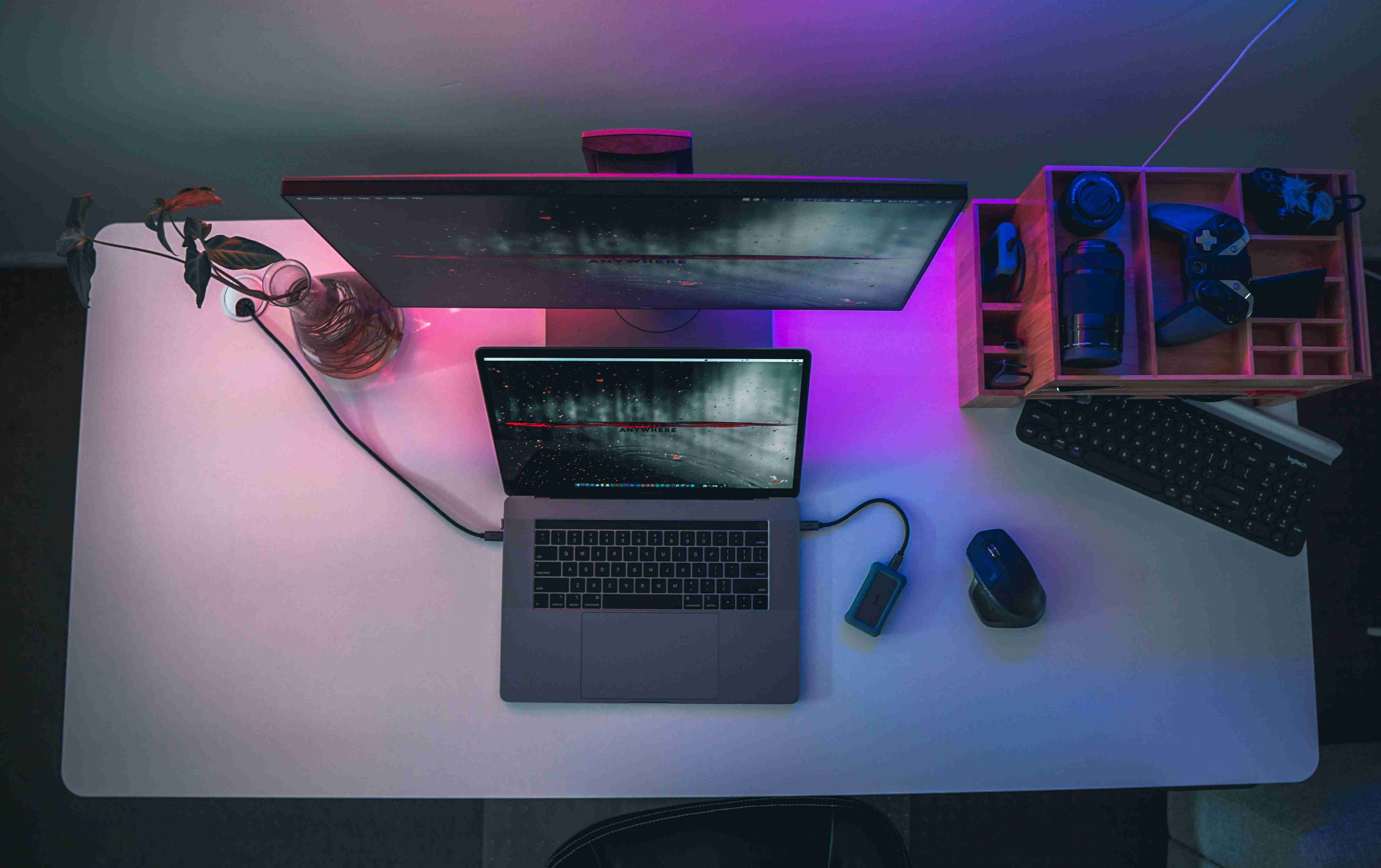
图8 公元前2000年:一个颇具兴味的切入点

图9 青铜礼器的出现与中原社会的转型

图10 二里头遗址地理位置

图11 二里头遗址卫星影像

图12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形器

图13 礼仪用器的制度化

图14 中国最早的近战兵器群

图15 二里头文化青铜器和西北、新疆青铜器的比较
就像现在的西服,肯德基和麦当劳,是一种流行品。甚至前些年藏区牧民居然还戴着嵌着红五星的红军帽,都是“礼失而求诸野”,在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就是最时髦的。尽管二里头在三千多年以前,当时还没有这样大的国家实体,但是它已经奠定了中国的雏形。玉石牙璋的辐射范围已经到了越南北部,跟《禹贡》九州的大致范围以及秦汉帝国统一疆域的范围大致相当。除了四大边疆之外,内地十八省适合农耕的区域,二里头那个时期的影响力已经基本上达到了,这样到后来才一点一点地奠定了中国的基础。那个时候的交通以水路为主,整个向四围辐射,张光直先生认为对青铜原料的获取很有可能是中原王朝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因为那是关系到国家命脉的。
在郑州商城时期,已能铸造大铜方鼎,方形器要比圆形器规格高一大截,前面说的模范中国、内模外范,都用于制造这类礼器。这套东西是显现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礼乐用品,后来都大量地出现。我们刚才说的“爵”,就是一千多年来一直沿用的一种酒器,现在都被画在门神上,此外还有“爵位”的说法,封官加“爵”,像这样的东西都是浸润于中国人的骨血里边的,还有许多细节需要探究。如果古代有九鼎的话,也应该是大方鼎,而不该像现在的网络游戏或者是多宝格里边想象中的鼎,那是国家命脉所在,所以我说从早到晚,古今一理。这种青铜重器是跟权力、政治和驭人之术相关联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想把司母戊大方鼎送给蒋介石做生日贺礼,蒋没敢接,因为这份礼太重了,这是国家重器。但是临去台湾之前,他还是舍不得,到了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看了一眼,临走的时候还想带走,又因为太重了不好带,八百多公斤,整个船装起来挺麻烦的。但是大量的艺术品目前还在台北故宫里存放着,他还是有传统的思想,就是想着国家命脉所在。
6
我们探究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国家的形成,有很多细节看不清楚,国家和文明不是一道门槛,而是一个过程,但是长程地看,前国家时代和国家文明还是泾渭分明的。这种向心、开放的聚落形态是属于原始民主制的,这样的模式跟这种封闭性、独占性、秩序性的聚落形态形成鲜明对比。不少著名学者在他们的书里都说,“不让看”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账本不让看、地图不让看、紫禁城不让看,它是封闭性的、独占性的,它很难形成广场上纪念碑式的东西,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大家看从二里头开始,整个大四合院的建筑、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一直到明清紫禁城,这是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如果说前几千年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是偏于缓慢发展的,那么从青铜进入中原以来的这一千年,从小的城址,一直到二里头、郑州商城、殷墟这样的大都邑,呈几何级的庞大发展。如果要形象地描述一下,就是金字塔的层级越来越多,金字塔塔尖越来越高,而这些青铜礼器都是在大的都邑里边出来的。所以,如果现在观察中国中西部农村,跟两千年以前,就是战国到汉代铁犁铧发明之后的农民生活,几乎是一样的,但我们不能说中国没有进步,还是要看都邑,看金字塔的塔尖。
本人近年的几本小书,先是《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最近还有《何以中国》(彩图版)、《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把整个两千年中国都城史给大家串了一遍。
前面叙述的是中国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早期的中国是土生土长的吗?我们的回答是,早期的中国既不是土生土长的,也不是完全外来的,而是建立在海纳百川吸收外来因素,到了当地又经过本土化吸纳、创造的基础之上的。把文明如果形容成流水的话,不如形容成病毒,如果大家觉得病毒不好听的话,就形容成细胞或者是基因,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复制的同时产生变异,可能变得完全不同,中国文明恰恰就是这么出来的。如果看一下全球更早的文明,就能意识到,早在一两千年之前,整个地中海东岸地区、中亚地区就有了比较发达的青铜文化,现在看来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自然障碍。大家想一想,分子人类学已经证明了,连我们的远祖旧石器时代的人都是从非洲一点点地走过来,文化渐进发展过来的,只要以时间换空间,没有什么是不可逾越的。何况在青铜时代,甚至都已经有了马车,在欧亚大陆上进行交流就更加通畅了。所以,下一步我们还要探究冶铜术,全球史探究方兴未艾,但是到了中国这个地方,由于西方学者研究吸纳我们的成果还有一定的时间差,所以还相对薄弱,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可以进一步为全球文明史的编纂做出贡献。我们如果放开眼界,就会发现以青铜冶铸为代表的一些外来的因素有东渐的趋势,很明显,这种交流和传递是一波一波的。我的下一本小书就想以“东亚青铜潮”为主题,以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为主线,从全球文明史的视角,来写这个宏阔的态势,探究中国是怎么诞生的。有种叫塞伊玛-图尔宾诺的文化现象在中亚地区最初出现年代比较早,可能对西北的齐家文化,甚至二里头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封闭的,我们的青铜文明的发生大量吸收了外来的文化因素。
除了青铜之外,从龙山到殷墟的千年之内,小麦、绵羊、黄牛、马、车,以及用动物骨头占卜的习俗、大规模杀殉这样的文化现象,带墓道的大墓,甚至甲骨文等等,我们还都没有找到源于中原的本土基础,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语言和文字也是这样,文字就更是个问题,文字是否一定要通过几千年的积累才能成型?契丹文字和日本文字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吸收外来的刺激和影响后产生,这是非常复杂的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甚至像二里头这样管控、驾驭大范围人类群团的政治模式,究竟是我们从无到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明,还是受到了外边的影响和刺激才形成的,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比如说兵马俑,古代中国人的解剖学常识是非常差的,兵马俑那样的非常逼真的东西是纯本土的吗?甚至我们现在也有同仁在研究,像秦汉帝国这样大的帝国统治方式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发明。要知道,在它二三百年之前,波斯帝国已经形成了,非常有意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懂考古,已经搞不好考古了,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是不是这样的道理?诸位年轻人外语非常好,一定要开阔眼界,在全球文明史的层面来看我们中华文明的形成。今后一定要从这样大的视野来做整合研究。
我们现在得出来的结论是,东亚大陆几个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文明都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东亚青铜潮”有西风东渐这样一个过程,青铜文明从中原地区再往东,到了山东偏西的地方,还没到胶东半岛,已经是公元前1400年的二里岗晚期了,相当于商代中期前后。青铜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时候,已经是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了。在日本,青铜是跟铁器一起传进去的,我们看这个态势是非常清楚的,中国是其中的一个链条。从自然地理上看,中国像个大盆地,所以才有这样的文化上的凝聚力,但对外也没有太多自然的阻隔,所以不断有文化因素传播进来。如果我们心态偏于狭小,就会把这个盆地当成一个大井,由于这口井太大,使得我们往往有遨游的感觉。比如说多元、一元,到最后都是在这个大井里边来思考问题的。吉林大学著名考古学家林沄教授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以内亚草原为中心的青铜文化向四外辐射,就像一个大漩涡向外飞洒着飞沫,外围一些青铜文化的产生都应是这些飞沫的组成部分。能够这样想,好多东西也就释然了。这就让我们感觉到,只有使思维复杂化,放开视野,才能更好地探究我们的中华文明。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123456@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